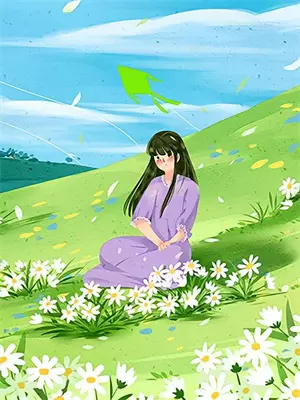一“跑警报了!”凄厉的喊声划破联大课堂的宁静。沈怀远拽着患疟疾的程嘉润跌进防空洞,
洞壁震落土块。他高烧中仍紧抱《诗经集注》:“书……不能丢……”敌机俯冲时,
我用身子护住他,却摸到他衣袋里硬硬的——是半块窝头。
————空袭警报是晌午过后拉响的。先前只有隐隐的嗡嗡声,
像夏日在芭蕉叶底下盘桓不去的牛虻,课堂里有人竖着耳朵听,心思便有些飘。
国文课的老先生正讲到《楚辞·九歌》里的“带长剑兮挟秦弓,首身离兮心不惩”,
声音苍凉,带着湖南口音的抑扬顿挫,在蒙自初夏湿热的空气里,
硬是劈开一小片沉郁顿挫的空间。但那嗡嗡声不肯散去,反而越来越重,
织成一张铺天盖地的网,从窗格外那方小小的、蓝得晃眼的天上罩下来。突然,
外面街上凄厉地炸开一声喊:“跑警报了——!”课堂里霎时间静寂,
连老先生的声音也戛然而止。仿佛只顿了一秒,
桌椅碰撞声、杂沓的脚步声、压抑的惊呼声便轰然炸开。学生们像决堤的水,朝着门口涌去。
我猛地从座位上弹起来,伸手就去拽旁边的程嘉润。他反应总是慢半拍,这会儿还撑着额头,
脸色蜡黄,嘴唇干裂起皮,眼神都有些涣散。滇南的疟疾,时冷时热地磨了他好些天,
人瘦脱了形,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穿在身上,空落落的。“嘉润!快走!
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,手下用力,把他从座位上扯起来。他浑身没什么力气,
大半重量都压在我胳膊上,跌跌撞撞地跟着人潮往外冲。外面早已乱成一团。
尖叫声、哭喊声、呼唤亲友名字的声音,
与那越来越近、越来越刺耳的飞机引擎轰鸣搅在一起,捶打着每个人的耳膜。
尘土被纷乱的脚步扬起,迷得人睁不开眼。天空上,几个黑点正在逼近,
带着一种不祥的、死神俯瞰般的从容。“去新防空洞!那边近!
”有人声嘶力竭地指着城外方向。我架着程嘉润,逆着些人流,
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城外新挖的那个大防空洞跑。他喘得厉害,呼出的气都是滚烫的,
身体一会儿筛糠似的抖,一会儿又软得往下溜。我咬紧牙关,胳膊死死箍住他的腰,
汗珠从额角滚下来,流进眼睛里,又涩又疼。“书……我的书……”他忽然挣扎着,
含糊不清地念叨。我低头一看,他另一只手里,竟还死死攥着那本上课用的《诗经集注》,
蓝布封面已经磨损得发毛,边角都卷了起来。都什么时候了!我心里一股无名火窜起,
真想给他吼回去,可看到他烧得通红却异常执拗的眼睛,那火气又瞬间被浇熄了,
只剩下酸涩的无奈。“拿着呢!没丢!”我喘着粗气吼道,脚下不停。
飞机的轰鸣声骤然放大,变成了撕裂布帛般的尖啸,就在头顶!
紧接着是炸弹落下时那令人头皮发麻的、“咻——咻——”的破空声。“卧倒!
”不知是谁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。我什么也顾不上了,拖着程嘉润,
朝着几步外那个黑黢黢的防空洞口,用尽全身力气扑了进去!几乎是同时,
身后传来地动山摇般的巨响!“轰!轰隆!”巨大的气浪从洞口卷进来,
夹杂着碎石和呛人的尘土。我们俩重重地摔在洞内凹凸不平的泥地上。
洞顶簌簌地往下掉土块,砸在头上、背上,生疼。整个世界都在摇晃,耳鸣声尖锐地持续着,
盖住了一切其他的声音。二黑暗中,我第一时间去摸身边的程嘉润。“嘉润?程嘉润!
”“……在……”他微弱地应了一声,带着颤音。我悬着的心落回一半,
这才感到自己背上火辣辣地疼,大概是刚才被崩飞的石子划伤了。洞子里挤满了人,
黑暗中只能听到一片粗重、惊恐的喘息和压抑的啜泣。空气里弥漫着土腥味、汗味,
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。敌机还在头顶盘旋,投弹的间隙,
能听到机枪扫射的“哒哒”声,像毒蛇的信子,舔舐着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。
每一次爆炸传来,洞壁就剧烈地一震,更多的泥土簌簌落下。程嘉润在我身边蜷缩着,
不住地发抖。我把他往怀里又紧了紧,试图用身体替他挡住可能落下的碎石。
他烫得像块火炭,隔着单薄的衣衫,那热度灼着我的皮肤。“冷……”他牙关打颤,
含糊地说。我摸索着,想把我的外套脱下来给他,却被他滚烫的手按住。他另一只手,
依旧死死抱着那本《诗经集注》,仿佛那是他的命。“书……不能丢……”他像是在梦呓,
声音断断续续,“‘岂曰无衣,与子同袍’……王……王于兴师……”都烧糊涂了,还在背。
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。想起刚来蒙自的时候,我们几个同学在南湖边,
看着烟波浩渺的湖水,他就是用这把清朗的嗓音,给我们讲《诗经》里的草木、爱情、家国,
眼睛里闪着光。他说,这书里藏着一个民族不灭的魂。可现在……又一波剧烈的爆炸声传来,
比之前更近,震得人五脏六腑都错了位。洞顶一块较大的土疙瘩猛地砸落,
正朝着程嘉润的头!我想也没想,整个身子扑过去,将他严严实实地罩在下面。
土块砸在我肩胛骨上,闷痛传来,我忍不住哼了一声。“怀远?!”他似被惊醒,
慌乱地要动。“别动!我没事!”我低喝,维持着保护的姿势不动。就在这紧密的贴合中,
我的手臂压在他侧身的衣袋上,隔着粗布,感觉到一个硬硬的、硌人的东西。不是书。
书的触感不是这样。这像是一块……半圆的、硬邦邦的饼子,或者……窝头。三我愣了一下。
白天我去校务处帮忙登记,领了这个月的口粮——掺了麸皮和沙子的“八宝饭”馒头,
回来分了他一个。我记得他当时吃得慢,说没什么胃口,只吃了小半个,
剩下的用纸包好塞进了口袋。难道……高烧到意识模糊,在敌机轰炸的生死关头,
还死死抱着这本破旧的诗集;而衣袋里,却揣着舍不得吃完、硬得硌人的半块窝头。
洞外的爆炸声渐渐稀疏,最终,那催命的引擎轰鸣也远去了。死里逃生的寂静笼罩下来,
只有洞里劫后余生的、长长的出气声,和低低的、压抑不住的哭泣。
警报解除的哨音迟迟响起,悠长而疲惫,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。人们开始互相搀扶着,
踉踉跄跄地往洞口挪动。光线重新透进来,刺得人眼睛发疼。我慢慢撑起身子,
感到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。程嘉润也挣扎着要坐起来,脸色依旧惨白,但眼神清明了些。
“怀远,你……你刚才……”他看着我肩上和背上的尘土,眼神里满是愧疚。我没说话,
只是伸手,探进他侧面的衣袋。他身体微微一僵。我摸到了。那半块窝头,硬得像石头,
边缘粗糙,安静地躺在他的口袋里,带着他的体温。我把它掏了出来。黄黑色,
掺着明显的麸皮,甚至能看到细小的沙粒,因为放久了,更加干硬结实,
静静地躺在我摊开的掌心里。程嘉润看着我手里的窝头,嘴唇动了动,想说什么,
最终却只是低下头,轻轻咳了两声。洞外,阳光猛烈,照着断壁残垣,
照着惊魂未定、满面尘灰的人群。生的气息,混杂着硝烟和血腥,扑面而来。
我握着那半块窝头,感觉它比任何东西都沉重。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,热辣辣的,
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四防空洞里摸出来的那半块窝头,最终我们谁也没吃。
回到借住的那间漏风的茅草房,我把那硬得像石块的东西掰开、敲碎,泡在烧开的热水里。
麸皮和沙粒沉了底,勉强能得一碗糊状的东西。程嘉润烧得迷迷糊糊,
被我强扶着灌下去小半碗,额上才算沁出些细汗,不再那么吓人地干烧着。他睡下了,
眉头却还皱着,不知是梦到了轰炸,还是别的什么愁烦。我坐在床边矮凳上,
就着窗外惨淡的月光,看那本被他拼死护住的《诗经集注》。书角在摔倒时磕破了,
我找房东阿婆要了点浆糊,小心翼翼地把它粘好。手指拂过书页上那些熟悉的诗句,
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墨字无声,却像针一样扎着心。家园,
早已在炮火中支离破碎,我们这些人,像无根的飘萍,被命运的风吹到这西南边陲。嘉润他,
大约是觉得,只要这些字、这些句子还在,那点儿文明的根脉,就还没断。
可根脉不能当饭吃。联大学生的“贷金”,名目好听,实则勉强果腹。
那掺了沙子稗子的“八宝饭”,吃得人肠胃绞痛;盐水煮的青菜,不见半点油星。
嘉润生病后,胃口更差,那份本就少得可怜的口粮,常常剩下。我起初以为他是真的吃不下,
直到防空洞里摸出那半块窝头,才恍然明白——他是省下来,
留给我这个还能跑能跳、消耗大的。这层窗户纸,我们谁也没捅破。只是后来,
我再领了口粮回来,当着他的面,必定先狠狠地咬上两大口,吃得狼吞虎咽,
嘴里还含糊地抱怨:“饿死我了,今天这馒头好像软和点!”然后不由分说,
把他那份塞到他手里,盯着他:“快吃,别磨蹭,凉了更硬,硌牙。”他看着我,
蜡黄的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有眼睫轻轻颤动一下,然后低下头,小口小口地,极其认真地,
开始吃他那份。我知道他未必吃得下,但那是一种无言的承诺,对我,也是对他自己。
疟疾这病,缠人。时冷时热,发作起来毫无规律。
有时我们正坐在简陋的图书馆——那是由旧庙改建的,四处漏风——看书,他会突然放下笔,
手指紧紧攥住衣襟,指节泛白。我知道,那是寒意来了。连忙脱下我那件同样破旧的外套,
给他披上。他裹紧衣服,身体仍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,像风中最后一片叶子。等到发冷过去,
高热袭来,他又会满脸潮红,额头滚烫,呼吸粗重。我便拿冷水浸湿了破毛巾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