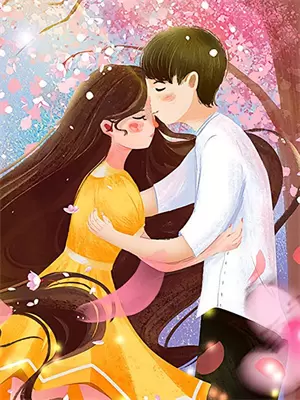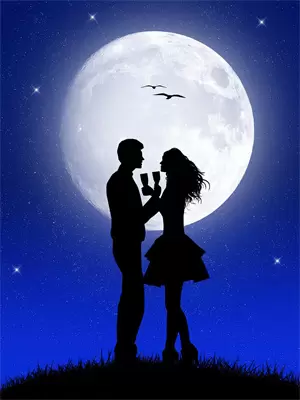林砚第一次见到苏清圆,是在一个能把人淋成落汤鸡的盛夏午后。
他抱着刚从旧书市淘来的一摞精装书,在公交站台下狼狈地躲雨。
雨势噼里啪啦砸在遮阳棚上,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脚。正当他踮着脚试图保护怀里的书时,
一把印着浅蓝桔梗花的伞忽然倾斜过来,遮住了他头顶的天空。“书会湿的。
”声音像浸过冰泉,带着点微不可闻的甜意。林砚转过头,看见个穿白衬衫的姑娘,
袖口卷到小臂,露出细瘦的手腕。她手里除了伞,还拎着个透明塑料袋,
里面装着几盒薄荷糖,包装上印着“清凉薄荷”四个字,和她的声音莫名契合。“谢、谢谢。
”他有些结巴,怀里的书沉甸甸的,让他一时腾不出手。姑娘没说话,
只是把伞往他这边又推了推。雨幕里,她的睫毛很长,被风吹得微微颤动,
像停着只欲飞的蝶。公交迟迟不来,站台下只有他们两个人,雨声成了唯一的背景音。
“你也等107路?”林砚没话找话,视线落在她塑料袋里的薄荷糖上。“嗯,去图书馆。
”苏清圆点头,忽然从袋里拿出一盒薄荷糖递过来,“这个,含着凉快。
”绿色的包装在雨里格外显眼。林砚接过来,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,像有微弱的电流窜过。
他剥开一颗塞进嘴里,清冽的薄荷味瞬间在口腔里炸开,
连带着刚才被雨浇出的燥热都散了大半。“很好吃,”他含着糖,说话有点含糊,“多少钱?
我转给你。”“不用啦,”苏清圆笑了笑,眼睛弯成月牙,“算谢礼,
谢你刚才帮我捡起掉在地上的书签。”林砚这才想起,刚才在书市门口,
他确实弯腰帮一个姑娘捡过一枚嵌着干花的书签。原来那时就见过了。公交终于来了,
两人一前一后上了车。林砚刷卡时才发现,自己的公交卡不知什么时候丢了。
他翻遍口袋也没找到零钱,正窘迫着,身后传来“滴”的一声——苏清圆用她的卡帮他刷了。
“下次再还我吧。”她轻声说,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林砚抱着书坐在她旁边,
心里像揣了颗刚化了一半的薄荷糖,凉丝丝又带着点甜。车窗外的雨还在下,
街景模糊成一片流动的水墨画。他偷偷看她,她正望着窗外,
侧脸的轮廓在雨雾里显得格外柔和。“你喜欢看书?”她忽然转过头问。“嗯,尤其是老书。
”林砚赶紧点头,指了指怀里的书,“这些是从旧书市淘的,有些还是民国时期的版本。
”“我也喜欢老东西,”苏清圆眼睛亮了亮,“图书馆里有很多旧期刊,我经常去翻。
”他们就这样聊了起来,从旧书聊到古籍修复,从城南的老槐树聊到巷尾的糖水铺。
林砚发现,苏清圆不仅懂书,还会画画,她的书签都是自己做的,刚才那枚干花书签,
花是她在郊外采的野菊。车到站时,雨小了些。苏清圆要去图书馆,
林砚的目的地离图书馆不远。“我送你到图书馆门口吧?”林砚说,把伞往她那边递了递。
“不用,雨快停了。”苏清圆摆摆手,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条,“这是我的联系方式,
如果你有有趣的旧书,或者想聊古籍修复,可以找我。”林砚接过纸条,
上面是她的名字和一串手机号,字迹清秀,像她的人一样。他赶紧把自己的手机号报给她,
看着她存在手机里。“那我先走啦。”苏清圆对他挥挥手,转身走进雨幕里,
浅蓝的伞像一朵盛开在雨天里的桔梗花。林砚站在原地,手里捏着那张纸条,
嘴里的薄荷味似乎还没散去。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图书馆门口,心里忽然觉得,
这个下雨的午后,或许是这个夏天最幸运的一天。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薄荷糖盒子,
又看了看纸条上的名字——苏清圆。或许,他们的故事,就从这颗雨天的薄荷糖开始了。
林砚回去后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苏清圆的手机号存进通讯录,
备注写了“桔梗花与薄荷糖”。他对着那行字看了半晌,指尖在拨号键上悬停许久,
终究还是没敢按下去。三天后的傍晚,他在整理从旧书市淘来的那批书时,
发现其中一本1930年代的《园艺杂志》里夹着张泛黄的书签。不是苏清圆那种干花样式,
而是用薄竹片削成的,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句“雨打芭蕉,闲敲棋子”。字迹娟秀,
边角已磨得发亮,显然被人摩挲过无数次。他心里一动,立刻想起苏清圆说过喜欢老东西。
犹豫片刻,还是编辑了条短信发过去:“在一本旧杂志里发现枚竹片书签,字很漂亮,
你或许会喜欢。”短信发出去的瞬间,他忽然有点紧张,像是把颗薄荷糖抛进了水里,
既期待那声轻响,又怕它化得太快。没过五分钟,手机震了震。苏清圆回了条语音,
背景里有翻书的沙沙声:“是哪种字体?民国时期的文人喜欢在书签上题小楷,
尤其是女性作者。”她的声音比那天在公交站更清晰些,带着点刚从书堆里抬起头的慵懒,
像浸了温水的薄荷,清润得让人心里发酥。林砚赶紧拍了书签的照片发过去,
又补充:“杂志是讲园艺的,说不定是位爱花草的人留下的。”“太巧了!
”苏清圆很快又回了消息,“我今天刚在图书馆翻到1929年的《花卉图谱》,
里面提到有人喜欢用竹片做书签,还会拓印花叶上去。这枚没拓花,但字里有股草木气。
”一来二去,两人就着这枚旧书签聊了起来。从竹片的产地聊到拓印技法,
林砚发现苏清圆不仅懂古籍修复,对传统工艺也颇有研究。她说自己祖父是做竹编的,
小时候常看祖父削竹片,那些薄如蝉翼的竹篾在他手里能变成花篮、竹扇,
还有各式各样的书签。“下次有机会,我给你看我祖父做的竹编书签,比这个更精致。
”她说。“好啊,”林砚立刻接话,心脏跳得有点快,“那……要不要一起吃个饭?
就当是谢谢你那天帮我刷公交卡,还有这枚书签的缘分。”屏幕那头沉默了几秒,
久到林砚以为自己唐突了,正想找补几句,苏清圆的消息跳了出来:“可以啊,
这周六下午图书馆闭馆早,我们在馆门口见?我知道附近有家老面馆,葱油面做得特别香。
”林砚几乎是立刻从椅子上弹了起来,手指飞快地敲:“好!就这么定了!”挂了电话,
他才发现自己手心都出汗了,对着镜子里傻笑的自己摇摇头,
转身把那枚竹片书签小心翼翼地放进丝绒盒子里——这得当成见面礼送过去才像样。
周六下午,林砚特意提前半小时到了图书馆门口。秋老虎还没退,日头晒得人发暖,
他却觉得比那天淋雨时还要紧张。正站在树荫下搓手,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:“林砚?
”回头就看见苏清圆,今天没穿白衬衫,换了件浅杏色的棉布连衣裙,头发松松地挽了个髻,
露出光洁的脖颈。她手里拎着个藤编小篮子,看见他就笑:“等很久了吗?”“没有没有,
我也刚到。”林砚赶紧摆手,目光落在她的篮子上,“这是……”“给你的。
”苏清圆把篮子递过来,“上次说的竹编书签,我找了祖父做的几个,
还有我自己拓的花叶书签,你看看喜不喜欢。”篮子里铺着层棉纸,放着五六枚书签,
竹编的纹路细密如织,拓印的荷花、兰草栩栩如生。林砚拿起一枚竹编的,
指尖能摸到竹篾的温度,心里忽然涌上股说不出的妥帖。“太好看了,”他由衷地说,
“比我那枚旧书签精致多了。”“各有各的好,”苏清圆笑着说,“旧物有旧物的故事,
新做的有新做的心意。”两人并肩往面馆走,阳光透过行道树的缝隙洒下来,
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林砚把丝绒盒子递给她:“这个给你,算是回礼。
”苏清圆打开盒子,看见那枚竹片书签,眼睛亮了亮:“真的有草木气!
你看这‘闲敲棋子’的‘敲’字,笔锋里都带着点轻脆感,像真的在敲棋子似的。
”她低头看书签的样子,睫毛在眼睑下投出小片阴影,林砚忽然觉得,
这画面比书签上的字还要动人。老面馆藏在巷子里,门口挂着块褪了色的木牌,
写着“老徐记”。老板娘是个胖阿姨,见了苏清圆就笑:“清圆来啦?还是老样子,
葱油面加个荷包蛋?”“嗯,再加一份,和我一样的。”苏清圆回头看林砚,
“这家的葱油面用的是新榨的菜籽油,葱炸得焦香,你肯定喜欢。”面端上来时,
果然香气扑鼻。金黄的葱油浮在面上,卧着个流心的荷包蛋,筷子一挑,
面条裹着油香滑进嘴里,熨帖得人心里暖洋洋的。“你经常来这儿?”林砚边吃边问。“嗯,
以前跟着祖父来的,”苏清圆说,“他总说这家的面有小时候的味道。”她提起祖父时,
眼里有怀念的光。林砚安静地听着,听她说祖父如何教她辨认草木,
如何在竹片上拓印第一片叶子,如何在她弄坏了他的竹编作品时,非但不生气,
还说“慢慢来,手熟了就好”。“祖父去年走了,”苏清圆轻轻搅着碗里的面,
“但每次来这儿吃葱油面,就好像他还坐在我对面,
絮絮叨叨地说竹篾要选向阳的竹子才坚韧。”林砚没说话,
只是把自己碗里的荷包蛋夹给她:“流心的,你应该喜欢。”苏清圆愣了愣,抬头看他,
眼里闪过一丝暖意,轻轻说了声“谢谢”。吃完面,两人沿着巷子慢慢走。
巷尾有个老太太在卖糖画,转糖画的转盘上画着龙凤花鸟。苏清圆站在那儿看了许久,
眼睛里带着点孩子气的向往。“想转一个吗?”林砚问。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
林砚付了钱,让她转。木指针转了几圈,稳稳地停在了“兔子”上。老艺人手起勺落,
琥珀色的糖稀在青石板上勾勒出只蹦蹦跳跳的兔子,耳朵长长的,尾巴短短的,可爱得很。
苏清圆小心翼翼地举着,阳光照在糖画上,晶莹剔透的,像块凝固的阳光。“真好看。
”她轻声说。“嗯,像你画的那些书签。”林砚说。苏清圆转过头看他,
夕阳刚好落在她眼里,漾着细碎的光。她忽然笑了,嘴角的梨涡浅浅的:“林砚,你知道吗?
薄荷糖放久了会受潮,但刚才那家面馆的葱油香,好像能记很久。”林砚的心猛地一跳,
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下。他看着她手里的糖兔子,看着她眼里的光,忽然明白,
有些味道比薄荷更持久,有些遇见,比雨天更绵长。他没说话,只是觉得,
这条飘着葱油香的巷子,还有她手里那只糖兔子,大概会和那个雨天的薄荷糖一起,
住进他往后的日子里。自那以后,林砚和苏清圆见面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。
有时是林砚在旧书市淘到有趣的孤本,特意绕到图书馆附近,
给苏清圆送去一本复印件;有时是苏清圆修复好了一页民国时期的乐谱,打电话叫林砚去看,
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页,讲油墨如何在时光里沉淀出温润的光泽。
他们会一起去图书馆闭馆后的老街散步。路灯昏黄,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,
偶尔有晚归的猫从墙头上窜过,惊起几片落叶。
苏清圆会带他去看巷子里那棵三百年的老银杏,说祖父以前常来这儿捡银杏叶做书签。
深秋时叶子黄透了,踩上去沙沙响,像踩着一整个秋天的私语。
林砚则带她去了自己常去的旧书店。店主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先生,
见了林砚就笑:“又带朋友来淘宝?
”苏清圆在堆满书的角落里翻到本1950年代的《民间剪纸集》,
书页间夹着张褪色的剪纸,是只笨拙的蝴蝶。她像捡到宝贝似的捧在手里,
眼睛亮晶晶的:“这个我能试着复刻出来,贴在书签上肯定好看。
”林砚看着她小心翼翼把剪纸夹回书里,忽然觉得,和她在一起的时光,
就像浸在温水里的茶,慢慢舒展,溢出清浅的香。转折发生在一个初冬的午后。
苏清圆给林砚打电话,声音里带着点急:“你能来趟图书馆吗?我发现了件麻烦事。
”林砚赶到时,见她正蹲在古籍修复室的地上,面前摊着一卷残破的画册。画纸脆得像枯叶,
边缘已经发黑,几处虫蛀的洞眼把画里的山水啃得支离破碎。“这是刚从仓库里翻出来的,
”苏清圆指着画册,语气里满是心疼,“是清代画家吴宏的山水册页,可惜保存得太差了,
好多地方都粘连在一起,一撕就碎。”林砚蹲下来仔细看,画册的纸页薄如蝉翼,
墨迹却依旧苍劲,能看出笔锋里的力道。他想起自己曾在一本老书里见过类似的修复案例,
赶紧说:“我记得有种‘雾润法’,用极细的水雾把纸页润开,再慢慢揭开……”“我试过,
但这纸太脆了,水雾多一点就会烂。”苏清圆叹了口气,指尖轻轻碰了碰画页,
像怕碰碎了时光,“馆长说要是修不好,可能就要封存起来了。”林砚看着她泛红的眼眶,
忽然说:“我们一起试试吧。我去找找相关的资料,你熟悉纸张特性,说不定能想出办法。
”接下来的一个月,两人几乎泡在了修复室里。林砚翻遍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修复文献,
甚至托人找来了民国时期修复大师的手稿复印件;苏清圆则一遍遍调试润纸的湿度,
用最细的羊毫笔蘸着特制的浆糊,一点点填补虫蛀的空缺。有次忙到深夜,
修复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人。台灯的光晕落在画册上,也落在苏清圆专注的侧脸。
她睫毛上沾了点细小的纸屑,像落了片雪花。林砚伸手想帮她拂掉,
指尖快碰到时又缩了回来,转而倒了杯温水递过去:“歇会儿吧,看你眼睛都红了。
”苏清圆接过水杯,指尖碰到他的,两人都愣了一下。她低头喝水时,耳尖悄悄红了。
“你说,古人画这画的时候,是不是也像我们这样,对着一张纸琢磨很久?”她忽然问。
“说不定比我们更较真,”林砚笑了,“毕竟是要留着给后人看的。”“那我们也算替后人,
留住点什么吧。”苏清圆望着画册,眼里有温柔的光。一个月后,
当最后一页画页被小心地抚平,贴在新的衬纸上时,两人几乎同时松了口气。
阳光透过修复室的窗户照进来,落在画册上,山水的纹路在光里仿佛活了过来,
连虫蛀的痕迹都被巧妙地补成了山间的云雾。馆长来看时,
忍不住拍着他们的肩膀感叹:“真是后生可畏!这册页能重见天日,多亏了你们。
”那天晚上,他们又去了那家老面馆。老板娘见他们脸上带着笑意,
打趣道:“今天有啥好事?看你们俩高兴的。”苏清圆没说话,
只是把自己碗里的荷包蛋夹给了林砚,和上次他给她时一模一样。林砚看着碗里的蛋,
忽然鼓起勇气说:“清圆,下个月城南有个古籍展,里面有吴宏的真迹,我们……一起去看?
”苏清圆抬起头,眼睛弯成了月牙,比上次在公交站见到时更亮。“好啊,”她说,
“刚好可以带着我们修好的册页去‘认亲’。”林砚看着她眼里的光,忽然觉得,
那些一起在修复室里熬过的夜,那些为了一页纸争论的细节,都成了藏在时光里的糖。
比雨天的薄荷糖更沉,也更甜。他想起苏清圆曾说,旧物有旧物的故事。或许,他们的故事,
也正在这些被修复的时光里,慢慢变得完整。古籍展在市美术馆开展那天,天气难得放晴。
林砚特意提前到了美术馆门口,手里拎着个纸袋,
里面是他早上去老字号买的桂花糕——苏清圆说过,她祖父以前总爱用桂花糕配茶。
苏清圆来得很准时,穿了件米白色的针织衫,手里捧着个长条形的木盒。
“我们修好的册页也带来了,”她把木盒递给林砚看,脸上带着点小骄傲,
“馆长说让它跟真迹‘打个招呼’。”林砚接过木盒,入手温润,是上好的楠木。
他打开看了眼,修复后的册页平平整整,补纸的纹路和原纸几乎融为一体,
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修补的痕迹。“比我想象中还好,”他由衷赞叹,“你补的云雾,
比原迹还多了点灵动感。”苏清圆被他夸得有点不好意思,耳尖微红:“是你找的资料管用,
那‘雾润法’的火候,全靠你抄的那几页手稿才掌握住。”两人边说边往里走。
展厅里很安静,柔和的灯光打在泛黄的纸页上,古画里的山水人物仿佛都在呼吸。
他们在吴宏的真迹前站了很久,那幅《秋山图》笔力雄健,山石的皴法苍劲有力,
和他们修复的册页风格如出一辙。“你看这里,”苏清圆指着画中一处瀑布,
“他用了‘破墨法’,墨色浓淡相破,才有这种流动感。我们修的那页里也有类似的技法,
当时总觉得缺点什么,原来少了这层墨色的层次。”林砚凑近看,
果然见墨色在纸上晕染出深浅变化,像真的有水汽在蒸腾。“以前只在书上见过说破墨法,
今天看真迹才懂,”他转头看向苏清圆,“跟你在一起,总能发现新东西。
”苏清圆正好也转过头,两人的目光撞在一起,空气里仿佛有细碎的光在跳。
她赶紧移开视线,指着不远处的展台:“那边还有清代的笺纸展,去看看?
”笺纸展台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彩色花笺,有的印着缠枝莲,有的描着兰草,
最显眼的是一叠洒金红笺,金粉在光下闪闪烁烁。“以前的人写信都用这种笺纸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