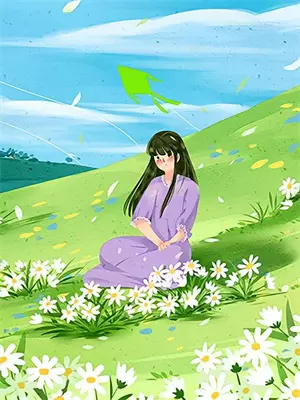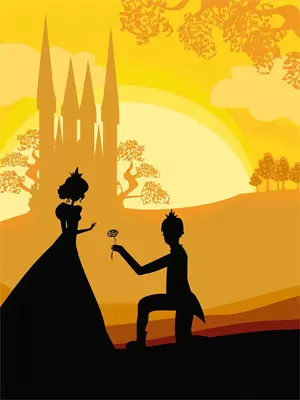暮春的雨,淅淅沥沥,连绵不绝,打在无相寺层层叠叠的青瓦上。雨水顺着屋檐滴落,
在石阶上敲打出清脆而孤寂的声响。年仅七岁的小和尚了尘,穿着略显宽大的灰色僧衣,
蹲在寺庙高大的山门檐下。他小小的身子蜷缩着,一只手揣在怀里,
紧紧攥着半块早上省下来的、已经有些发硬的麦饼,却没有吃。了尘那双清澈乌黑的眼睛,
一眨不眨地紧盯着山门前那条蜿蜒向下、被雨水浸得泥泞不堪的小路。他在等人。他知道,
就算是这样的天气,她也一定会来。果然,没过多久,迷蒙的雨幕中,
一个瘦小的身影出现了。她撑着一把破旧的油纸伞,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水里,
小心翼翼地护着怀里那个用破旧却洗得干净的布包。是阿禾,山脚下一户农家的小姑娘。
等她走近了,能看清她素色的布裙下摆早已沾满了斑驳的泥点,裤腿也湿了大半,
小脸上挂着雨珠,却带着明媚的笑容。阿禾看到了檐下的了尘,眼睛一亮,
嘴角不自觉地上扬,加快脚步跑到他面前,声音变得雀跃:“了尘哥哥!
娘让我给你送热米糕来了!刚出锅的,可香了!”了尘看着她被雨水打湿的额发,
心里莫名一紧,下意识地将手里那半块舍不得吃的麦饼往身后藏了藏,
仿佛那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他是无相寺方丈在外化缘时捡回来的弃婴,
是寺里用百家饭喂大的。他天资聪颖,三岁便能磕磕绊绊地熟读《心经》,
五岁时就能与师兄们辩论佛经中的微言大义,寺里所有的师父都说他是天生佛子,慧根深种。
可每当面对阿禾这双亮晶晶、毫无杂质的眼睛时,他那颗平日里诵经念佛时古井无波的心,
总会不受控制地跳得快几分,快得让他有些慌张。他努力板起小脸,学着师父们的样子,
双手合十,稚嫩的声音带着故作的老成:“阿弥陀佛。师父说,
出家人……不能妄受俗家之物。”“这哪是俗家之物!”阿禾撅起小嘴,
根本不理会他的推拒,直接伸手将尚带着体温的布包塞进他怀里,动作熟练又自然,
“这是我自己偷偷省下来留给你的!快拿着,还热乎呢!”说着,她踮起脚尖,伸出小手,
仔细地拂去了尘僧衣肩头溅上的雨水,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关切,“雨凉,别站在风口,
当心着凉了。”怀里的米糕传来温热的触感,透过粗布僧衣,熨贴着皮肤。
了尘感觉自己的小脸有些发烫,他翻遍了自己能看懂的那些佛经,
也不明白这莫名的燥热从何而来。他望着阿禾说完话就转身跑开、消失在雨幕中的背影,
直到那小小的身影彻底不见,才低下头,看着怀里的布包,双手合十,
在心里默默地、也是第一次,真正困惑地念了一句:“色即是空……”往后的岁月,
如同山涧的溪流,潺潺而过,带着春夏秋冬的印记。春天,山野间的映山红开得烂漫,
阿禾会采来最鲜艳的一束,偷偷放在了尘禅房的窗台上。夏天,
她会抱着一个在井水里浸得冰凉的大西瓜,坐在寺门外的石墩上,耐心等待他早课结束。
秋天,金黄的银杏叶落满庭院,她会小心翼翼地用叶子拼出了尘盘坐念经时的模样,
然后兴奋地朝他招手,声音穿过寂静的寺院:“了尘哥哥,快来看!我拼得像不像你?
”冬天,寒风凛冽,她会不畏严寒,揣着一个暖手的汤婆子,踏雪而来。每次递过汤婆子时,
她都会顺势把自己冻得通红的小手飞快地塞进了尘的怀里,眼睛弯成好看的月牙,
带着狡黠的笑意:“了尘哥哥,我的手好冷,快帮我捂捂!”了尘的佛法日益精深。
他十二岁时,便已能深入浅出地为寺里的师兄们讲解晦涩难懂的《金刚经》,言辞机锋,
常得师父们赞许。可只要面对阿禾的笑容,他依然会像七岁那个雨天一样,手足无措,
心跳失序。有一天,阿禾捧来一只翅膀受伤、奄奄一息的小麻雀,
眼中满是怜悯和期待:“了尘哥哥,它好可怜。等它的伤好了,我们一起去后山给它放生,
好不好?”了尘接过那只脆弱的小生命,看着阿禾亮晶晶的、充满信任的眼睛,
郑重地点了点头。为了不辜负这份期待,他竟忘了寺里就有精通医术的师叔,自己冒着烈日,
漫山遍野地寻找草药,亲自捣碎了,小心翼翼地敷在小麻雀的伤口上。
小麻雀伤愈振翅的那天,两人一起跑到无相寺后山的望星台。夕阳西下,
漫天晚霞将天空染成瑰丽的锦缎。阿禾兴奋地抬起手,指向天边那一片绚烂:“了尘哥哥,
你快看!像不像你禅房里挂的那幅《极乐图》?”了尘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,
余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了她被晚霞染红的侧脸上。少女的轮廓在光影中显得格外精致,
眼眸里映着霞光,熠熠生辉。他看得微微出神,半晌才猛地惊醒,慌忙低下头,
紧紧闭上眼睛,双手合十,急促地念诵着“阿弥陀佛”,试图压下那如擂战鼓般狂跳的心。
十五岁,了尘按照无相寺的寺规,受了沙弥戒,换上了更为庄重的僧袍,
眉宇间多了几分沉稳与庄严。而阿禾,也出落得亭亭玉立,每次站在寺庙山门前,
那清丽的身影总能引得往来香客驻足侧目。她送来自己亲手晒制的笋干时,
看着了尘愈发清俊却也愈发疏离的侧脸,内心忐忑,
终于鼓起勇气轻声问:“了尘哥哥……你以后,会一直待在寺里吗?”了尘捻着佛珠,
目光低垂,看着脚下的青石板,声音平静无波:“出家人早已了却烦恼根,
红尘俗世皆是虚妄,自然以寺为家。”阿禾眼中的光彩瞬间黯淡了下去,像被风吹熄的烛火。
她低下头,用力咬了下嘴唇,再抬起时,脸上挤出一个有些勉强的笑容:“……我知道了。
那……以后有空,我还来给你送的。”了尘没有抬头,只是捻动佛珠的手指,
微不可察地停顿了一下。十七岁那年的夏天,一场罕见的暴雨席卷了山村,
阿禾家的土坯房屋顶被冲垮,她的爹娘在慌乱中躲避不及,都摔成了重伤。
她家里的顶梁柱倒了,她的天仿佛也塌了。阿禾抱着年幼的弟弟,
在依然飘着雨丝的无相寺山门前,哭得撕心裂肺。那一刻,
了尘脑中什么清规戒律、什么男女有别,全都顾不上了。他几乎是冲出了山门,
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,不顾旁人惊诧的目光,轻柔而坚定地扶起几乎瘫软在地的阿禾,
带着她和她弟弟,急匆匆地去寻寺里精通医术的师叔。在阿禾爹娘养伤的那段艰难日子里,
了尘总会想方设法偷偷溜下山。他笨拙地帮着阿禾料理家务,照顾卧床的双亲,
煎药、喂饭、擦拭身体,甚至挽起僧袍,和泥搬砖,帮着修缮那垮塌的屋顶。
阿禾则总是默默地跟在他身边,在他累得满头大汗时,适时地递上一碗热粥,
声音沙哑却温柔:“了尘哥哥,歇会儿吧,别累坏了你自己。
”看着阿禾日渐消瘦的身影和那双因为劳累、担忧而总是通红的双眼,
了尘第一次对自幼信奉的佛法产生了怀疑。佛说慈悲,普度众生,
可他此刻只想度眼前这一个女子脱离苦海。这究竟是慈悲,还是……别的什么?他不敢深想。
等到阿禾爹娘的伤势渐渐痊愈,了尘开始刻意地疏远她。他不再轻易见她,
也不再收她送来的任何东西。了尘以为,距离可以斩断那不该滋生的妄念。可阿禾还是来。
有时在他禅房的窗台上放一朵带着露水的野花,有时放两个还温热的馒头,有时,
她什么都不放,只是静静地站在窗外,哼唱起小时候了尘教给她的那首童谣,声音轻轻的,
带着说不出的哀愁。了尘在禅房内,背对着窗户,盘膝坐在蒲团上,手里紧紧攥着佛珠,
一遍又一遍地默诵《心经》。然而,经文越念越快,
心底那个叫“阿禾”的影子却越来越清晰,思念非但没有减少半分,反而像藤蔓一样,
缠绕得他几乎窒息。十九岁那年,方丈大师正式提出,要为了尘受具足戒,成为真正的比丘。
这意味着他將正式与红尘俗世做最彻底的切割。受戒的前一夜,
了尘在自己狭小的禅房里枯坐了一夜。青灯古佛,寂寂无声,唯有木鱼声歇。他的脑海中,
不受控制地反复浮现出与阿禾相识十几年来的一点一滴。七岁雨天的米糕,夏天冰凉的西瓜,
秋天金黄的银杏叶,冬天温暖的汤婆子,望星台上她被晚霞映红的侧脸,
她家遭难时无助的哭泣,以及她日渐成长、清晰明媚的容颜……他发现自己心里有万般不舍,
如同钝刀割肉,疼痛绵长。可他自幼长于佛门,佛法早已融入骨血,
让他不敢、也不能去违背那心中的信仰。天快蒙蒙亮时,他推开禅房的门,第一眼,
就看见了那棵古老银杏树下站着的身影。阿禾穿着一身崭新的红布裙,
在黎明前的青灰色调中,鲜艳得如同燃烧的火焰。她曾经说过,这是山脚下村子里,
姑娘们出嫁时才会穿的颜色。她看着他,眼眶里盈满了水雾,
声音却异常清晰和坚定:“了尘哥哥,我喜欢你。从七岁那年第一次给你送米糕开始,
就喜欢了。”阿禾顿了顿,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,“我不奢求你能为我放弃佛法,
我……我会一直等着你。等你有一天,
或许……”了尘只觉得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,闷痛得让他几乎无法呼吸。
他抬手死死地捂住胸口的位置,张了张嘴,喉咙却像是被堵住了一般,半晌,
也说不出一句回应,更说不出一句挽留。了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,看着阿禾说完这句话后,
最后深深地望了他一眼,然后决绝地转身,那抹刺目的红色,
一点点消失在晨雾弥漫的山路尽头。直到那身影彻底消失,了尘才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,
猛地转身冲回禅房,紧紧关上门,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。
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疯狂默念着《心经》,试图驱散脑海中那抹鲜红的影子,
可眼泪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,顺着脸颊滑落,滴在灰色的僧衣上,晕开一抹深色的湿痕。
庄严的受戒仪式上,戒香点燃,灼烫在头顶,带来一阵剧烈的刺痛。然而了尘却浑然不觉,
他的全部心神,都被脑海中那抹挥之不去的、阿禾身穿红裙的背影所占据。那红色,
比戒香的火光还要炽烈,烫伤了他的心。他最终成了无相寺最年轻的比丘,
众人皆赞他年少持重,是活菩萨转世,将来必能光大佛门。可只有了尘自己知道,
他那颗本该圆满无暇的佛心,早已有了一个名叫“阿禾”的缺口,永难填补。
阿禾没有离开村子。她拒绝了所有上门提亲的人,态度坚决得让父母无可奈何。
她对谁都说:“我在等一个人。我会一直等下去。”秋末的一天,了尘下山办事归来,
在寺庙后山那条僻静的小路上,被阿禾拦住了。她低着头,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,声音发颤,
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坚定:“了尘哥哥……我们……我们试试好不好?我不缠着你,
也不告诉任何人。就每个月十五,在这棵老槐树下见一面。我给你带我自己做的点心,
你……你陪我说说话,就一会儿,行吗?”了尘看着她眼中那几乎卑微的乞求,
想起暴雨中她哭红的双眼,想起她身穿红布裙时那决绝而悲伤的背影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