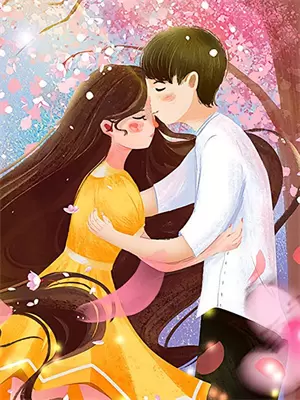第一章:噩梦重生林晚秋猛地从床上坐起,胸口剧烈起伏,冷汗浸湿了单薄的碎花衬衣。
她大口喘着气,茫然地环顾四周。昏暗的煤油灯,糊着旧报纸的土坯墙,
墙上挂着印有“农业学大寨”字样的泛黄镜框,身下是硬得硌人的木板床,
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霉味和泥土气息。这不是她临终前住的、充满消毒水味的冰冷病房。
这里是……七十年代,她插队落户的陕北小河村?她的知青点宿舍?
她难以置信地抬起自己的手,皮肤虽然因常年劳作而粗糙,却充满年轻的韧劲,
不是晚年那双布满褶皱和老年斑的手。记忆如同决堤的洪水,汹涌而至。她记得,
1975年,她为了留在城里顶替母亲工矿名额的机会,被恋人张志强花言巧语哄骗,
把名额让给了他。他信誓旦旦承诺,等他站稳脚跟就想办法接她回城结婚。结果呢?
张志强一去不回,很快就在城里攀上了高枝,娶了车间主任的女儿。而她,林晚秋,
则因为把名额让给“未婚夫”的行为不符合政策,被卡在了农村,
最终嫁给了村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王老五,开始了噩梦般的一生。
家暴、贫困、疾病、丧子……生活的苦难将她磋磨得面目全非。
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,她才看到一丝微光,
却因为多年劳作拖垮的身体和早已荒废的学业,连考三年都名落孙山,最终遗憾终身,
郁郁而终。她……这是回来了?回到了命运的转折点——1975年春天?
张志强还没回城的时候?“晚秋,你醒啦?做噩梦了?
”同屋的女知青赵晓梅被她的动静惊醒,揉着眼睛嘟囔道。林晚秋深吸一口气,
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不是梦,这真实得刺痛的触感,这年轻身体里蓬勃的活力,都在告诉她,
她真的重生了!“没事,晓梅,你睡吧。”她低声应道,声音还带着一丝颤抖,
但眼神已经迅速变得坚定。她轻轻下床,走到窗前。窗外月色如水,洒在寂静的村庄上。
前世几十年的苦难和悔恨,如同烙印般刻在她的灵魂深处。既然老天给了她重来一次的机会,
她绝不会再重蹈覆辙!张志强!王老五!还有那些曾经轻视她、践踏她的人……这一世,
她要把命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!首先,第一件事,就是绝不能把回城的名额让给张志强!
这个自私自利的渣男,休想再吸她的血!其次,她要读书!她记得很清楚,
距离恢复高考还有两年多时间。这两年,她必须争分夺秒,重新捡起课本。
前世她学习成绩本就不错,只是被生活磨灭了希望。这一世,她一定要考上大学,
走出这片黄土地,去拥抱本该属于她的广阔天地!想到这里,
林晚秋只觉得一股久违的热流涌遍全身。她不再是那个认命、懦弱的林晚秋了。从这一刻起,
她是为自己而活的战士!第二天天刚蒙蒙亮,林晚秋就起来了。她利落地收拾好床铺,
拿出藏在箱子最底层、已经有些卷边的高中课本。
语文、数学、政治……这些陌生的符号和公式,此刻在她眼中却如同稀世珍宝。
她正小心翼翼地拂去书本上的灰尘,宿舍门被敲响了。“晚秋,是我,志强。
”门外传来一个熟悉的、带着几分急切的男人声音。林晚秋动作一顿,
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寒意。来了。讨债鬼来了。第二章:撕破伪装林晚秋深吸一口气,
压下心头翻涌的恨意,脸上努力装出平静的样子,走过去打开了门。门外站着的,
正是年轻时的张志强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
脸上带着他惯有的、看似真诚的笑容。若在前世,林晚秋会被这笑容迷得晕头转向,但现在,
她只看到他眼底深处那抹急于算计的精明。“晚秋,你起来啦?我听说大队部昨晚开会了,
回城顶替的名额定下来了,是你妈那个纺织厂的工作对吧?”张志强挤进门,
迫不及待地压低声音问道,眼神热切。林晚秋不动声色地后退半步,与他拉开距离,
淡淡地“嗯”了一声,继续整理着手中的书本,没有看他。张志强似乎没察觉到她的冷淡,
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,自顾自地继续说道:“太好了!晚秋,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!你看,
我们之前说好的,你把名额让给我,我先回城站稳脚跟。你放心,我跟我爸妈都说好了,
等我一进厂,就想办法开介绍信,咱们就结婚!到时候我再活动关系,把你也弄回去!
”又是这一套!前世他就是用这套说辞,把她骗得团团转,
让她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唯一回城的机会。林晚秋心中冷笑,面上却故作犹豫:“志强,
这样……能行吗?政策允许吗?我听说顶替名额查得很严,要是被发现了……”“哎呀,
你放心!”张志强拍着胸脯,信誓旦旦,“我都打听好了!就说是咱们快结婚了,
你身体不好,不适应农村生活,自愿把名额让给未婚夫。大队支书那边,
我塞两包烟再说说好话,肯定没问题!为了我们的未来,这点风险值得冒!
”他说得情真意切,甚至伸手想来抓林晚秋的手。林晚秋猛地缩回手,抬起头,
目光清冷地看着他:“为了我们的未来?张志强,你真的是为了我们吗?”张志强一愣,
脸上闪过一丝慌乱,但很快掩饰过去:“晚秋,你这是什么话?当然是为了我们啊!
你难道不相信我?”“我相信你?”林晚秋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,“我相信你回城后,
就会立刻忘了还在农村吃苦的我?我相信你会娶一个对你前途毫无帮助的知青?张志强,
别把我当傻子了。”“林晚秋!你胡说什么!”张志强脸色变了,声音也拔高了几分,
带着被戳穿心思的恼羞成怒,“我好心好意为你规划,你居然这么想我?
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?”“没人跟我说什么。”林晚秋平静地打断他,眼神锐利如刀,
“是我自己想的。这个回城名额,是我妈提前病退才换来的,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。
我不会让给任何人,特别是你。”她一字一顿,清晰地说道:“张志强,我们完了。
从现在起,你走你的阳关道,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这个名额,我要自己用。”“你!
”张志强气得脸色铁青,指着林晚秋,你了半天,才咬牙切齿道,“好!好你个林晚秋!
没想到你是这种自私自利的人!算我张志强看错你了!没有我,你以为你一个女的,
拿着名额就能顺顺利利回城?你别做梦了!我告诉你,你会后悔的!”面对他的威胁,
林晚秋只是冷冷地转过身,继续整理书本,丢下一句:“后不后悔,是我的事。不劳你费心。
请你出去,我要看书了。”张志强看着她油盐不进的样子,知道再说无益,
只得恨恨地一跺脚,摔门而去。巨大的声响惊动了隔壁宿舍的人。
林晚秋听着他远去的脚步声,紧紧攥着拳头,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,
但心中却是一片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。第一步,她终于迈出去了。与渣男彻底切割,
守住回城的希望。然而,她知道,这仅仅是开始。张志强绝不会善罢甘休,
回城的名额也未必能轻易到手。前路,依然布满荆棘。但她不怕。从重生那一刻起,
她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她拿起那本《代数》,深吸一口气,翻开了第一页。知识,
才是她通往未来的唯一阶梯。第三章:名额风波林晚秋与张志强彻底闹翻的消息,
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小河村传开了。人们议论纷纷,大多觉得林晚秋不识好歹,
放着张志强这样看起来有“前途”的知青不要,非要守着那个不一定能落到实处的回城名额。
张志强果然没闲着,他开始在知青点和村里散布谣言,说林晚秋思想落后,怕苦怕累,
一心想回城享受,甚至暗示她为了名额可能用了不光彩的手段。
他还特意去找了大队支书李有才,递上好烟,一番“痛心疾首”的陈述,
暗示林晚秋不安心农村建设,把名额给她是浪费国家资源。这些风言风语,
林晚秋或多或少听到了。她心中冷笑,却并不急于辩解。在这个讲究成分和表现的年代,
空口白牙的争论毫无意义,她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和过硬的理由。
她首先找到了知青点的点长,一位姓王的老知青,为人还算正直。林晚秋没有哭诉,
而是冷静地陈述了事实:回城顶替是国家政策,
名额属于她个人;她与张志强只是普通同志关系,
不存在“让名额”的说法;张志强的谣言已对她造成困扰,希望组织能主持公道。接着,
她比以往更加卖力地参加生产队劳动。割麦、锄地、挑粪,这些重活累活,她从不偷奸耍滑,
甚至比男知青干得还拼命。汗水浸透了衣衫,手掌磨出了血泡,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。
她要让所有人都看到,她林晚秋不是怕吃苦,她只是要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!劳动之余,
所有休息时间都被她用来复习功课。田间地头,她揣着写满公式的小纸条默背;夜深人静,
她点着煤油灯啃噬那些晦涩的定理。她的勤奋和坚韧,渐渐改变了些周围人的看法。
同屋的赵晓梅从一开始的不理解,到后来主动帮她打掩护,让她能多点时间看书。
最关键的一步,是面对大队支书李有才。李有才是个典型的农村基层干部,有些滑头,
看重实际利益。那天,林晚秋被叫到大队部谈话。李有才端着搪瓷缸,吸着烟袋,
慢悠悠地说:“小林啊,你和张志强同志的事情,闹得沸沸扬扬,影响很不好嘛。
关于这个回城名额,你要理解,队里也要综合考虑嘛。你看,志强同志是男同志,
表现一直不错,回去更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……”林晚秋静静地听着,等他说完,
才不卑不亢地开口:“李支书,我明白组织的难处。但我认为,
判断一个青年能否为社会主义出力,不应该只看性别。党的政策号召‘男女平等’,
‘妇女能顶半边天’。我自问下乡以来,劳动从不怕苦怕累,思想积极要求进步,
这是有目共睹的。”她顿了顿,目光清澈而坚定:“这个名额,
是我母亲为支持国家建设提前病退换来的,于情于理于政策,都应当属于我。
如果因为一些不实谣言就剥夺我的资格,恐怕难以服众,也违背了政策的公平原则。
我相信支书您一定会秉公处理。”她没有哭闹,没有哀求,而是摆事实、讲政策、论道理,
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李有才有些意外地看着这个平时看起来有些文静的女知青,
没想到她如此条理清晰,句句点在要害上。更重要的是,林晚秋悄悄打听到,
李有才的儿子明年也想参军,需要政审材料。而她恰好知道,县里分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,
是她母亲一位老同学。这个信息,她看似无意地提了一下,暗示如果名额顺利,
她家会记住这份人情。软硬兼施之下,李有才的态度明显松动了不少。他沉吟半晌,
终于表态:“嗯,小林同志说的也有道理。你放心,大队部会严格按照政策办事,
不会偏听偏信。你回去好好劳动,不要有思想包袱。”从大队部出来,林晚秋长长舒了口气。
她知道,这一关,她暂时闯过去了。但张志强绝不会甘心失败,他一定还有后手。果然,
几天后,公社突然派人下来,要重新审核小河村知青的回城名额情况,
重点就是林晚秋这个“有争议”的名额。风暴,即将来临。
第四章:绝地反击公社工作组的到来,让小河村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。
带队的是公社革委会一位姓钱的副主任,面色严肃,一来就召集大队干部和部分知青开会,
矛头直指林晚秋的回城名额问题。显然,张志强在背后没少活动。
他在会上“义正辞严”地发言,声称林晚秋近期劳动表现是“伪装”,目的是骗取回城机会,
其思想本质是“资产阶级享乐主义”,
并暗示她与某些“有问题”的家庭关系密切影射林晚秋母亲那位当副书记的老同学,
试图把水搅浑。一些平时与张志强交好、或者得到他些许好处的知青和村民,也开始附和,
说些模棱两可、对林晚秋不利的话。形势对林晚秋极为不利。赵晓梅急得直跺脚,
偷偷拉林晚秋的袖子,让她赶紧说点什么辩解。林晚秋却异常镇定。她知道,在这种场合,
情绪化的争吵只会落入下风。她静静地听着所有的指责和质疑,
直到钱副主任把目光投向她:“林晚秋同志,对于大家反映的情况,你有什么要说的吗?
”林晚秋站起身,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场众人,最后落在钱副主任脸上,
声音清晰而沉稳:“钱主任,各位领导,同志。关于我的回城名额,我想说明几点。
”“第一,政策依据。知识青年回城顶替父母工作,是国家和省市有明确文件规定的政策。
我母亲符合病退条件,我本人符合顶替条件,手续齐全,合理合法。
不存在任何‘骗取’行为。”“第二,劳动表现。我下乡五年,
每年的工分记录都在大队部有案可查,各位领导和乡亲们都可以核实。
我自问对得起‘知青’这个称号,从未给小河村抹黑。近期的劳动,
我只是延续了一贯的态度,何来‘伪装’之说?难道积极劳动也成了错误?”“第三,
思想动机。我想回城,是因为国家有这个政策,我想继承母亲的工作,
为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贡献力量。这与我是否怕苦怕累无关。如果按照某些同志的逻辑,
想回城就是思想落后,那国家制定这个政策的意义何在?
岂不是所有想回城的知青思想都有问题?”她逻辑严密,句句在理,
直接戳破了张志强扣下的“大帽子”。会场上一时鸦雀无声。钱副主任也微微皱起了眉头,
似乎在思考。林晚秋趁热打铁,拿出了她的“杀手锏”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红宝书,
以及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。“至于我的思想状况,口说无凭。
这是我这段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,还有我结合农村实际,
写的一份关于科学种田、提高亩产的建议书。请领导审阅。我一心向党,追求进步,
绝不是某些人污蔑的那种落后分子!”这是她熬夜写出来的,
结合了前世的一些见识和今生的思考,虽然稚嫩,但在这个年代,
足以显示出一个青年的“思想觉悟”和“文化水平”。钱副主任接过那几张纸,
仔细看了起来。会场上的风向开始悄悄转变。一些原本中立的干部和村民,
开始觉得林晚秋这个女娃娃不简单,说话有条有理,还写了学习心得和建议书,
比只会空口指责的张志强显得更有水平。李有才支书见状,也适时开口,
肯定了林晚秋平时的劳动表现,并委婉表示名额问题应按政策办。张志强脸色煞白,
他没想到林晚秋准备得如此充分,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。他还想争辩,
却被钱副主任用眼神制止了。最终,公社工作组经过再次核实和讨论,
宣布:林晚秋的回城顶替名额符合政策,予以确认。同时,
不点名地批评了某些捕风捉影、不利于团结的言行。消息传出,知青点一片哗然。
赵晓梅抱着林晚秋又跳又笑。而张志强,则在一片异样的目光中,灰溜溜地躲回了宿舍。
林晚秋站在院子里,感受着阳光的温暖。这场风波,她赢了。不仅保住了名额,
更在众人面前树立了一个坚强、有头脑的形象。她知道,回城的路铺平了。但她的目标,
远不止是回城当一名纺织女工。她抬头望向远方,群山之外,是更广阔的世界。高考,大学,
那才是她真正的战场。第五章:告别黄土回城名额的风波过后,
林晚秋在小河村的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。原先那些背后议论她“傻”或“不识抬举”的人,
如今看她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敬佩和忌惮。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女知青,
关键时刻竟有如此魄力和手腕,连公社下来的干部都能说得心服口服。张志强彻底蔫了,
见了林晚秋都绕道走,整日阴沉着脸。他的名声在这次事件中受损严重,
原本围着他转的几个跟班也疏远了他。林晚秋对此漠不关心,
她的心思早已飞向了更远的地方。手续办得出奇地顺利。大队部盖章,公社审核,
县知青办批复……一个月后,
秋终于拿到了那张沉甸甸的、盖着鲜红大印的“知识青年回城审批表”和粮油关系转移证明。
离别的日子定在初秋。天高云淡,黄土高原上吹来的风已带了些许凉意。临走前夜,
林晚秋将宿舍里用不上的脸盆、暖水瓶、一些旧衣物,分送给了关系较好的几位村民和知青,
特别是赵晓梅。赵晓梅拉着她的手,眼圈红红:“晚秋,回了城别忘了我们啊!你这一走,
我心里空落落的。”林晚秋心里也有些发酸。几年的知青生活,有苦难,也有温情。
这片黄土地,留下了她太多的汗水和青春印记。她拍拍赵晓梅的手:“晓梅,有机会来省城,
一定找我。你也别放弃学习,国家不会一直这样的,总有需要知识的时候。”第二天清晨,
队里派了辆驴车送她去公社坐长途汽车。不少村民和知青都来送行。
老支书李有才也破天荒地说了几句勉励的话。驴车吱吱呀呀地走在村口的土路上,
扬起淡淡的尘土。林晚秋回头望去,小河村在晨雾中渐渐模糊,
那些熟悉的窑洞、麦垛、还有远处连绵的黄土高坡,都将成为记忆中的风景。
她没有太多离愁别绪,心中充满的是对新生活的憧憬和紧迫感。两年半,
距离恢复高考还有两年半!她必须争分夺秒!长途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七八个小时,
终于抵达了省城。熟悉的城市气息扑面而来,虽然同样是灰扑扑的色调,满街的蓝灰绿服装,
但毕竟有了楼房、汽车和相对丰富的物资供应。回到家,看到明显苍老了许多的父母,
林晚秋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前世,她让父母操碎了心,晚年也未能尽孝。这一世,
她绝不会再让父母失望!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!”母亲抹着眼泪,上下打量她,“瘦了,
也黑了,在乡下吃苦了。”父亲话不多,只是默默地把她的行李接过去,眼里满是欣慰。
家的温暖暂时驱散了旅途的疲惫。但林晚秋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中。第二天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