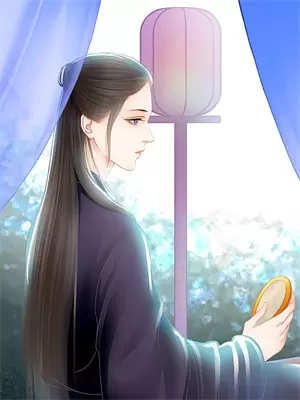高二的暑假,像一杯逐渐冷却的温水,沉闷,黏稠,带着一种无所事事的倦怠。
我将自己的世界收缩在这栋位于村西头的二层小楼里,收缩在二楼这间临窗的房间里。
父母在城里打工,几个月才回来一次,空旷的房子里只剩下我和一条名叫老黑的老狗。
书桌紧挨着窗户,堆满了习题集和课本。台灯是我最忠实的伙伴,在无数个夜晚,
它洒下的椭圆光晕就是我全部的疆域。窗外,是熟悉得近乎刻板的农村夜景。远处,
零星几户人家的灯火如同沉入墨海的孤舟,微弱地闪烁着。近处,则是大片大片的黑暗,
被田埂、树丛和更远处的老鸦山轮廓切割成沉默的几何形状。夜晚的声音很单调,
风吹过屋后那片竹林,发出永无止境般的沙沙声,偶尔夹杂着几声遥远的犬吠,
更衬得四周万籁俱寂。院门的矮墙上,装着一盏声控感应灯。
它平日里像个恪尽职守又沉默寡言的哨兵,只有当人车经过,发出足够响动时,
才会骤然亮起,投下一片昏黄得有些暧昧的光域,
短暂地照亮门前那一小片泥地和一个孤零零的稻草垛,随后便悄然隐没于黑暗。
它的存在感很低,低到我几乎从未在意过它,就像不会在意自己的呼吸。
那是七月中旬一个普通的夜晚。白天的燥热尚未完全散去,
空气里飘浮着泥土和植物蒸腾的气息。我像往常一样伏案学习,直到脖子酸痛,眼睛干涩,
才关掉了台灯。房间瞬间被柔软的黑暗包裹,只有窗外稀疏的月光,
勉强勾勒出窗框和家具模糊的轮廓。疲惫像潮水般涌来,我很快沉入了睡意的边缘。
就在意识即将模糊的那一刻,眼皮外部感知到的黑暗被驱散了,一种昏黄的光透了进来。
是院门口的感应灯亮了。大概又是哪只野猫跑过去了吧,或者是不安分的黄鼠狼。
村里这种事很常见。我连眼皮都懒得抬,含糊地想了一下,翻了个身,面朝墙壁,
试图重新捕捉那流失的睡意。几秒钟后,那光亮消失了。黑暗回归。我调整了一下姿势,
准备继续入睡。可是,没过一分钟,也许更短,那片昏黄的光又一次穿透了我的眼皮。
怎么又亮了?我微微蹙眉,依旧没有睁眼。或许是那只猫在门口徘徊?光亮再次熄灭。这次,
我等了稍长一会儿,睡意似乎被这反复的打扰驱散了一些。就在我以为它不会再亮,
心神稍定之时——它又亮了。这次我不得不睁开了眼睛。房间里,
天花板上映着一片模糊晃动的水渍般的光斑。光源来自窗外,稳定地存在着,
不像是有活物在移动时该有的晃动。它就那么亮着,固执地亮着。我下意识地竖起耳朵,
窗外的世界依旧只有风声和竹叶的摩擦声,没有猫叫,没有脚步声,什么都没有。那片光,
像是凭空自己亮起来的。它亮了多久?我感觉至少有兩三分钟,或许更长。
时间在黑暗和寂静中被拉长,变得难以估量。然后,毫无征兆地,光灭了。
房间重新陷入黑暗,但这黑暗似乎与之前不同了,它带着一种重量,压在我的胸口。
我的耳朵变得异常敏锐,努力地在一片寂静中分辨着任何微小的声响。只有风,
依旧不知疲倦地吹着。几分钟后,就在我的意识再次开始模糊,即将坠入睡眠时,
那片昏黄的光,又一次,毫无道理地,固执地,亮了起来。我的心跳莫名地漏跳了一拍,
随即开始不规律地加速。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,像细小的冰屑,悄无声息地撒在我的皮肤上。
我依旧躺着,没有动,但全身的肌肉却不由自主地绷紧了。我盯着天花板上那片光斑,
它纹丝不动,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人,正静静地站在院门口,一动不动,触发了这盏灯,
并且……一直没有离开。这个念头不受控制地钻进我的脑海,带着一股阴森的寒意。
我猛地闭上了眼睛,不敢再看。光亮持续着,这次感觉格外漫长,我甚至在心中开始默数,
一、二、三……数到接近一百五十,那光才倏地熄灭。然而,这一夜的折磨才刚刚开始。
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,那盏灯就像一只抽搐的眼睛,在深沉的夜色里间歇性地明灭。
有时间隔几十秒,有时几分钟,毫无规律可言。有一次,它甚至亮了足足有十分钟!
那片昏黄的光晕死死地钉在院门口,稳定得令人窒息。我始终没有勇气起身去看一眼,
只是僵直地躺在床上,感觉自己像被钉在了砧板上,被动地承受着这无声的、反复的凌迟。
直到窗外天际泛起一丝极其微弱的、鱼肚般的青白色,那盏灯才终于彻底沉寂下去,
仿佛它也随着夜晚一同沉睡了。第二天,我是被透过窗户的阳光晒醒的。头昏沉沉的,
像灌了铅。坐在床上,昨晚的经历如同一个怪诞的梦。我趿拉着拖鞋下楼,
老黑趴在院子的树荫下,看到我,懒洋洋地摇了摇尾巴。我特意走到院门口,
仔细打量着那片泥地。除了几片被夜露打湿的落叶和一些细碎的尘土,什么也没有。
没有脚印,没有动物抓挠的痕迹。那盏感应灯安静地挂在墙上,
白色的塑料灯罩边缘沾着一点蛛网,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。“大概是坏了吧。”我对自己说,
试图用这个最合理的解释来驱散心头那团说不清道不明的阴霾,“电路老化,
或者感应器太敏感了。”我甚至想着,要不要找邻居懂电的王叔来看看。
但一种莫名的、微妙的抵触情绪让我放弃了这个念头。我不想让外人知道这件事,
仿佛说出来,就会打破某种脆弱的平衡,将昨晚那令人不安的感觉坐实。
白天的村庄是鲜活而嘈杂的,阳光驱散了夜晚的诡秘。我和伙伴们去河边钓了会儿鱼,
汗水浸湿了衬衫,蝉鸣在头顶聒噪不休。直到夕阳西下,暮色四合,
那种若有若无的不安才又随着降临的黑暗,悄然爬回心头。夜幕再次降临。我坐在书桌前,
台灯亮着,书本摊开,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耳朵总是不自觉地偏向窗外,
警惕着那可能再次亮起的光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窗外一片漆黑,感应灯一直没有动静。
我几乎要说服自己,昨晚确实只是个意外,灯可能真的只是临时故障。就在我心神稍定,
准备继续做题时——那片熟悉的、昏黄的光,又一次,穿透了窗户,投射在天花板上。
它又来了。我的笔尖顿在纸上,留下一个浓重的墨点。
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攥了一下。我强迫自己不要去看,不要去想,
只是死死盯着眼前的习题。但那光的存在感太强了,它像一个无声的宣告,
提醒着我昨晚的一切并非幻觉。它亮了大概一分钟,灭了。几分钟后,又亮起。这一晚,
它虽然没有像前一晚那样频繁闪烁,但断断续续的亮起,每次都精准地打断我的思绪,
将一种细微却持续的不安注入我的血液里。我开始害怕关灯,台灯的光成了我脆弱的保护层,
仿佛只要我这边的光不灭,窗外的异常就无法真正侵入。随后的几个晚上,这种情况持续着。
那盏灯总会在深夜莫名亮起,亮起的时间毫无规律,有时一夜数次,有时则长时间沉寂,
在我几乎要忘记它时又突兀地闪现。我开始睡眠不足,眼下挂上了浓重的黑眼圈。
白天的我也变得有些神经质,总会下意识地瞥向院门的方向。一晚,感应灯又亮了。
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骚扰,正烦躁地拉上窗帘,试图隔绝那令人不适的光线。就在这时,
一阵极其轻微的声响,却像一根冰冷的针,猝不及防地刺入了我的耳膜。“咚……”非常轻,
非常缓,带着一种小心翼翼,仿佛怕惊扰了夜的宁静。我的动作瞬间僵住,
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向了耳朵。“咚……”又一声。间隔了大概十几秒。声音的来源很清晰,
是从楼下传来的,方向正是……院门。有人在敲门。不是那种理直气壮的、找人的敲门,
也不是风吹动门板的声音。这声音太轻了,太有耐心了,带着一种诡异的试探性。
我用被子蒙住头,试图隔绝那声音,但它像一条滑腻的蛇,执着地往耳朵里钻。声音很轻,
间隔很长,我必须全神贯注,屏住呼吸,才能捕捉到那缓慢得令人心焦的节奏。
“咚……咚……咚……” 它不像是在呼唤,更像是一种确认,确认屋里是否有人,或者,
确认我是否醒着。那一夜,我在被子里蜷缩成一团,冷汗浸湿了额发,
敲门声断断续续持续了很久,直到天色将明才彻底消失。第二天,我脸色苍白,食欲全无。
老黑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异常,用它湿漉漉的鼻子蹭了蹭我的手心。我看着它,
很想问它昨晚听到了没有,但它只是茫然地看着我,摇了摇尾巴。
敲门声在随后的夜晚成了新的固定节目。它一天比一天清晰,那“咚……咚……”的声响,
仿佛不再只是敲在木门上,而是直接敲在我的心臟上,敲在我的骨头上。我的精神变得很差,
白天对着书本发呆,字迹在眼前晃动却无法进入大脑;晚上则陷入一种焦虑的等待中,
等待那必然响起的、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我开始避免在晚上下楼,
甚至连堂屋的灯都不敢去开。那扇厚重的木质院门,原本只是家里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,
现在却仿佛成了连接内外两个世界的禁忌边界。我反复检查门栓,确认它是否插得牢固,
仿佛这样就能阻挡住门外那未知的存在。一晚,那敲门声变得格外清晰,也格外执着,
节奏甚至比平时快了一些,带着一种隐隐的不耐烦。
一股混合着极致恐惧和被逼到绝境的、莫名的愤怒,像酒精一样冲上了我的头顶。
我受够了这种躲在暗处的折磨!我要看看,到底是什么东西!被这股冲动驱使着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