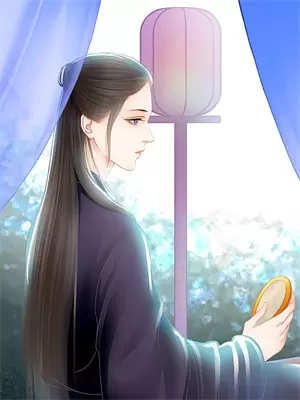1. 黔桂铁路支线的崇山峻岭间,晨雾还未散尽,
钢钎与岩石碰撞的叮当声就已刺破山林的寂静。父亲李铁山背着磨得发亮的铁锤和钎具,
大步走在筑路队的最前面,粗糙的手掌布满老茧,
那是二十多年石匠生涯和铁路隧道开凿留下的印记。——作为石工组领头人,
父亲隐隐有些担忧,这条铁路隧道已耗了他们八个月,再有百米就能贯通山腹,
可这最后一段硬岩,却邪门得让人心里发毛。“都打起精神来!
争取雨停前把这截硬岩啃下来!”父亲的声音洪亮如钟,回荡在开凿出的隧道里。
他身后跟着二十余名石工,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,
每个人的工具包上都挂着一块小小的青石挂件——那是父亲亲手凿的,说是能保平安。
父亲八岁就被爷爷送到邻村的石匠铺学徒,抡锤、凿石、雕纹,
十三岁就能独立打造整套石磨。十四岁入路后,这份精湛的石匠技艺让他在筑路队崭露头角,
很快就成了石工组的组长。隧道开凿最考验精准度和耐力,
父亲总能凭借过人的经验判断岩石的纹理,避开危险的断层,
这些年带领团队啃下了不少硬骨头。此刻,工作面已经推进到山腹,
隧道顶部用松木支架牢牢撑住,防止塌方。父亲指挥着众人分工:三人一组,一人掌钎,
两人挥锤,轮流作业。钢钎在岩石上留下一个个凿痕,石渣簌簌落下,
自有搬运队的人用竹筐运出去。“嘿!加把劲!”掌钎的老王喊了一声,
将一根铁钎稳稳抵在选定的位置。挥锤的是年轻力壮的小李和小张,两人默契十足,
铁锤高高举起,又狠狠落下,精准地砸在钎尾。就在这时,
意外突然发生——当小李和小张的铁锤同时砸下时,
就听“哐当”一声闷响老王掌着的那根铁钎竟像戳穿窗纸般齐齐没入了岩壁之中,
只留下一小截钎尾露在外面。正在不远处检查支架的父亲听到动静,
立刻快步走了过来:“怎么了?出什么事了?”“组长,
你看……”老王指着没入岩石的铁钎,声音都有些发颤,“刚才一锤下去,钢钎就掉进去了,
像是……像是里面是空的。”父亲皱起眉头,蹲下身仔细查看。
他伸手摸了摸铁钎周围的岩石,又用手指抠了抠缝隙里的石屑,脸色渐渐变得凝重。
“确实不对劲。”他沉吟道,“按常理,花岗岩密度均匀,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空洞。
但钢钎几乎全部没入,大概率是打到了空腔的边缘。”二十出头的小王正跟在父亲身后,
他是组里最毛躁的,平时总爱对着山壁上的纹路瞎琢磨,这时,他突然快步走上前,
说“李叔,你看这石头纹路,咋跟别处不一样?像刻了东西似的。”父亲没有搭话,
他站起身,拍了拍手上的灰尘:“这样,顺着这个方向,再多加几根钎,集中力量砸,
看看能不能把这层岩石打穿,弄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。”众人听父亲这么说,
心里稍稍安定了些。毕竟在隧道里遇到各种突发状况是常事,有经验丰富的父亲在,
大家总觉得有主心骨。很快,又有几根铁钎被牢牢固定在岩石上,四名石工轮流挥起铁锤,
朝着同一个点猛砸下去。“咚!”“咚!”每一锤都用足了力气,岩石的震动越来越明显。
打到第六锤时,突然传来几声清脆的“叮当”声,像是铁钎撞到了什么空荡的地方,紧接着,
面前的石壁猛地一颤,随即“哗啦”一声巨响,整块岩石裂成了好几块,
顺着工作面滚落下来,扬起一阵厚厚的粉尘。粉尘慢慢散去,
一个黑漆漆的洞口出现在众人眼前,约莫有井口大小。
一股难以言喻的恶臭瞬间从洞口喷涌而出,像是腐烂的尸体混合着潮湿的霉味,直冲鼻腔。
众人猝不及防,纷纷捂住鼻子后退,胃里翻江倒海,好几个人都差点吐出来。
“这……这是什么味道啊?”小张皱着眉,忍不住干呕了几声。“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?
”老王伸长脖子,试图看清洞口内部,却只看到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,
那股恶臭仿佛带着无形的压迫感,让人浑身发毛。父亲站在最前面,强忍着恶心,
眯起眼睛盯着洞口。他多年的石匠直觉告诉他,这个突然出现的黑洞,
绝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黑洞的边缘参差不齐,却绕着一圈模糊刻痕。那些符号扭曲如蛇,
既不是工地常用的开山标记,也不是当地苗人的图腾——更诡异的是,矿灯的光扫过符号时,
灯芯竟“噼啪”炸出火星,光线瞬间暗了几分。符号线条锋利得像烧红的铁钎刻上去的,
在潮湿的空气里泛着妖异的暗青色,像极了人凝固的血痂,
凑近了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、类似檀香的冷香,与那股恶臭格格不入。“大家退后,
离洞口远一点。”父亲沉声下令,同时从工具包里掏出矿灯,“小李,再带两个人回营地,
取防护面具、照明设备和防爆服,剩下的人把备用的绳索拿来,其他人在这里警戒,
不许擅自靠近洞口!”父亲的声音稳得可怕,但他知道,
他握着绳索的手在微微发抖——从事石匠三十多年,他见过塌方、见过岩爆,
却从没遇到过这样邪门的事。矿灯的光束照进黑洞,只能照亮洞口附近的一小片区域,
再往里,就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,仿佛一个蛰伏的巨兽,正无声地凝视着他们。
那股恶臭依旧弥漫在隧道里,夹杂着一种莫名的寒意,让所有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
“别碰!”父亲的喝声刚出口,小王的指尖已经碰到了洞壁。他像被烙铁烫到般猛地缩回,
疼得原地乱跳,指腹上赫然出现道焦黑伤口,形状竟与洞口符号分毫不差。更骇人的是,
那伤口周围的皮肤开始泛青,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皮下游走,小王吓得哭出声:“李叔,
我手麻……麻得像不是自己的!
”父亲慌忙掏出随身携带的雄黄酒——这是出发前当地苗寨老人塞给他的,
说能“驱山邪”——泼在小王伤口上,“滋啦”一声白烟冒起,青气才渐渐褪去。
空气瞬间冻住,连洞外的雨声都像停了。父亲盯着黑洞,感觉有双眼睛在里面盯着他们,
那股无形的寒意顺着脊椎往上爬,让他后颈的汗毛全竖了起来——从事石匠三十年,
他见过塌方、遇过岩爆,却从没像现在这样,被纯粹的“恶意”包裹着。
2.小李和另外两名工人应声而去,隧道里只剩下父亲和其余七名石工。
矿灯的光束在黑洞与岩壁间来回晃动,将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,
空气中的恶臭虽被众人用衣角捂住口鼻稍稍阻隔,却依旧顽固地钻入鼻腔,让人胸口发闷。
“组长,你说这洞里面,会不会是以前的老矿坑啊?”老王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,
试图用闲聊打破这压抑的氛围。他在筑路队干了十几年,见过的奇事不少,
但像这样凭空出现的黑洞,还是头一次遇上。父亲没有立刻回答,而是举着矿灯,
仔细观察洞口边缘的岩石。刚才瞥见的那些纹路,
在灯光下变得清晰了些——那是一些粗细不均的刻痕,弯弯曲曲地交织在一起,
像是某种简化的图腾,又带着几分诡异的韵律,绝非自然侵蚀的痕迹。“不像是矿坑。
”父亲的声音低沉,“矿坑的岩壁会有明显的开采痕迹,而且这符号……”他顿了顿,
眉头皱得更紧,“有点像老辈石匠说的‘镇物符’,但又不完全一样。”“镇物符?
”旁边的小张好奇地凑过来,“就是用来镇压不干净东西的那种?组长,你别吓唬我们啊。
”“我不是吓唬你们。”父亲收起矿灯,目光扫过众人,“在隧道里干活,小心驶得万年船。
不管里面是什么,在防护设备没到之前,谁都不能靠近。”他一边说,
一边从工具包里拿出几根粗麻绳,“来几个人,把绳索固定在旁边的支架上,
等下探查的时候用得上。”众人连忙应声动手,将绳索的一端牢牢系在松木支架上,
另一端垂到洞口附近,做好了应急准备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
隧道外的鸟鸣和风声隐约传来,与洞内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那股恶臭似乎越来越浓,
甚至开始让人头晕目眩。“怎么还没回来?”老王看了看手表,有些焦躁地踱步,“按理说,
回营地取东西,半个时辰也该到了。”他的话音刚落,
隧道入口的方向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众人精神一振,以为是小李他们回来了,
可走近了才发现,只有小李一个人,而且他脸色惨白,衣衫凌乱,像是受了极大的惊吓。
“小李?其他人呢?你怎么这副样子?”父亲连忙迎上去,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。
小李大口喘着粗气,嘴唇哆嗦着,好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:“组……组长,出事了!
小张和老刘……他们在路上晕倒了!我喊了半天都没反应,只能先跑回来报信!”“什么?
”众人脸色骤变。小张和老刘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,怎么会突然晕倒?“具体是怎么回事?
你们在路上遇到什么了?”父亲的语气带着一丝急切,双手紧紧抓住小李的肩膀。
小李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,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东西:“我们走了没多远,
就觉得身后凉飕飕的,像是有人跟着。一开始以为是风声,
可后来……后来我听到身后有奇怪的脚步声,回头一看,什么都没有。再往前走了几步,
小张突然喊头晕,然后就直挺挺地倒下去了,老刘想去扶他,也跟着倒了……我吓得不行,
只能先跑回来找你们!”父亲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。这深山老林里,虽然常有野兽出没,
但小李描述的情况,显然不像是野兽所为。难道和这个黑洞有关?“走,我们去看看!
”父亲当机立断,转身对老王说,“你带两个人在这里守着洞口,不许任何人靠近。
其他人跟我走,去救小张和老刘!”“组长,那这里……”老王有些犹豫,
毕竟洞口的未知危险也让人不安。“这里暂时不会有大问题,当务之急是救人。
”父亲的语气不容置疑,“记住,无论听到什么声音,都不要轻易离开支架附近。
”交代完后,父亲带着剩下的四人,跟着小李朝着隧道入口跑去。刚走出没几步,
身后突然传来老王的惊呼:“组长!不好了!洞口……洞口好像有东西在动!
”父亲心里一沉,立刻回头望去。只见矿灯的光束下,那个黑漆漆的洞口里,
似乎有一团模糊的影子在蠕动,而且那股恶臭瞬间变得浓烈了数倍,让人几乎窒息。
“你们先去送小张和老刘回营地,我回去看看!”父亲当机立断,转身就往洞口跑。
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,如果现在不查清洞口的情况,后果不堪设想。其他人也想跟着回去,
却被父亲喝住:“别过来!这里危险,你们快去救人,我马上就来!”父亲独自跑回洞口,
举着矿灯对准洞内。他仔细看去,发现那竟然是一堆缠绕在一起的藤蔓,
只是这些藤蔓的颜色异常深暗,像是被墨汁浸泡过,而且上面还长着一些密密麻麻的小刺,
散发着淡淡的腥味。“原来是藤蔓。”父亲稍稍松了口气,但随即又觉得不对劲。
这隧道深处阴暗潮湿,长出藤蔓并不奇怪,可这些藤蔓怎么带着如此诡异的气息?
他正想再靠近些观察,突然注意到藤蔓的根部,似乎缠绕着什么东西。矿灯的光束聚焦过去,
父亲的瞳孔瞬间收缩——那是一只帆布手套!隧道入口的方向传来了同伴的呼喊声,
显然是担心他的安危。父亲定了定神,对着洞口大喊:“老王,看好这里,
千万别让其他人进去!我去去就回!”说完,他转身朝着隧道入口跑去,
脑海里却反复回响着那声微弱的呻吟,以及洞口边缘那些诡异的符号。
3. 小张和老刘被抬回营地时,脸色惨白如纸,呼吸微弱得几乎察觉不到。
4. 队医紧急检查后,只说两人像是中了某种邪祟,脉搏紊乱,体温异常,
却查不出任何外伤或中毒的痕迹,只能先给他们喂了些安神的草药,用被子裹紧保暖。
营地的气氛瞬间变得恐慌起来。工人们聚在帐篷外,窃窃私语,眼神里满是不安。
有人说黑洞里藏着山里的精怪,小李他们惊扰了对方,
才遭了报应;也有人说二十年前这里就发生过类似的怪事,只是被上面压了下来,
没几个人知道。“都别瞎猜了!”父亲的声音打破了混乱,
“现在当务之急是照顾好小张和老刘,等天亮后联系上级,派专业的医生来。至于黑洞的事,
没我的命令,谁也不许再议论,更不许靠近!”父亲的威望在筑路队向来很高,
他的话让躁动的人群渐渐平静下来。
可二十岁入路后一直跟着爸爸已经“征战”过两条路段的我能看出,
他紧锁的眉头始终没有松开,握着玉佩的手也一直没有放松——自从从黑洞旁回来,
他就把爷爷传下来的信物——那块石匠印章从脖子上摘了下来,反复摩挲着上面的纹路,
像是在寻找什么答案。突然,父亲轻咦了一声,匆匆站起来,
一边吩咐我去准备面罩、绳索和照明工具,一边利索地穿戴起来。
他让我去通知几个信得过的人过来开会。待通知的人到了以后,
父亲开门见山地说“现在那个黑洞横在那里,工期又紧,
要绕过黑洞另外开凿隧道恐怕来不及。
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去探探黑洞是怎么回事”老王一听,惊得瞪大眼睛,连声说“老李,
不要冲动,你没看见已经有两个晕倒了吗?”父亲摇了摇头,沉着地说:“刚才我观察过了,
那个洞口的藤蔓可能以前是会伤人的,但现在这些藤蔓应该是已经干死了,伤不了人。
我带上装备,就在洞口看看。可以的话,就把洞口附近的那具尸体弄上来,
也可以找到点线索,总比现在大家一筹莫展地在这里猜测强。”大家见父亲主意已定,
就细化了进洞的路线、细节及装备。让我当父亲的助手,
老王和老张带着几个年轻人守住洞口,随时注意我们下洞时绑在身上的绳索,发现不对劲,
就把绳子拉出来。商议妥当后,我们一行人进入隧道,向着黑洞出发。
许是已经敞了几个小时的缘故,洞口的恶臭味没有那么浓烈了。
我们把绳索牢牢拴在顶部承重钢索上,父亲第一个系好安全扣,把矿灯调到最亮,
缓缓探身进洞。洞里比洞口看着宽敞,里面是条人工开凿的甬道,岩壁打磨得光滑,
却覆着层墨绿色苔藓,指尖摸上去又冷又黏,像沾了层死人的皮肤。
在洞口看到的那些藤蔓堆积在洞口附近,一只已经发黑的发布手套被紧紧缠住。
一条甬道伸向黑洞洞的远处。走了约莫十米,甬道突然开阔成七八平米的密室。
矿灯光柱扫过,众人倒吸冷气:地面散落着锈蚀工具,断柄钢钎上还卡着碎骨,
变形安全帽里嵌着半颗牙齿,旁边躺着具完整骸骨。骸骨已有些风化,
但藏青色制服残片还在,那是早期铁路工人的工装,布料糟朽得一触就碎,
却在骸骨胸口位置,凝着块发黑的血渍。最诡异的是骸骨的右手,呈握拳状,
指骨几乎嵌进掌心。父亲用撬棍轻轻拨开,一块半截玉佩掉了出来,青白色玉质温润,
边缘磕痕处泛着淡淡的血丝,上面的莲花纹与他贴身佩戴的石匠印章纹路,
一模一样——那个是爷爷传下来的信物,说是李家石匠的“命根子”。父亲摩挲着玉佩,
突然感觉一阵刺骨的凉意从指尖窜到心口,玉佩竟自动贴合在他掌心,像是长在了皮肤上。
他猛地抬头,发现密室顶部竟也刻满了那种暗青色符号,密密麻麻的,
像无数双眼睛正盯着他们。更诡异的是,随着矿灯晃动,那些符号竟在缓缓流动,
组成一句模糊的苗语——父亲曾跟苗寨老人学过几句,勉强认出是“擅入者,魂归石下”。
父亲示意我不要多言,伸手用力拉了三下绳索。这时我们刚才定下的暗号:拉一下,
表示是安全状态;拉两下,表示可以下来人;拉三下,
表示发现的东西需要带着包裹物下来搬运。过了几分钟,
老王带着三个年轻人带着绳子和篷布跟着我们放置的马灯指引,来到了密室。
虽然眼前的骸骨让他们既吃惊又害怕,还是忍着惧意,裹好骸骨运出黑洞。刚刚出洞,
我仿佛听到了一阵晦涩的低语。但看同行人的表情,似乎他们都没有听到,
我便以为是自己多想了。将骸骨抬出黑洞时,雨刚好停了,
夕阳把洞口的石头染成诡异的暗红色。筑路队队长赵奎闻讯赶来,
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总穿件洗白的中山装,眼神阴鸷,此刻看到玉佩,脸色“唰”地白了,
脚步踉跄了一下,像是见了鬼。“就是个早年失踪的工人,修老铁路时掉下去的,
没什么稀奇。”赵奎的声音发颤,眼神躲躲闪闪,挥挥手道,“找个乱葬岗埋了,
黑洞连夜填上,耽误了工期谁都担不起!”“赵队,这符号和骸骨都不对劲,是不是该上报?
”父亲追问,却被赵奎狠狠瞪了一眼:“李铁山,做好你的活就行,少管闲事!
”说完就转身离开了,背影显得有些仓促。夜幕刚降,营地就炸了锅。
有人说傍晚看到黑洞方向飘着个白影子,飘得离地半尺,头发披到腰上,
走过的地方草叶全成了焦黑色;有人说听见女人哭,哭声顺着风钻到帐篷里,
帐篷里的油灯就会自动熄灭。取工具的小张突然发起高烧,脸烧得通红,
皮肤下竟浮现出淡淡的符号纹路,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:“别凿了,
它要出来了……真的要出来了……”更怪的是,他的高烧用退烧药不管用,
苗寨老人送来的草药敷在额头上,草药瞬间就变成了黑色粉末。父亲越想越不对劲,
凌晨时分,悄悄溜到存放骸骨的临时棚屋。矿灯光打在骸骨上,
他突然发现骸骨的臼齿上有个极小的刻痕——是个“李”字,刻得极深,
这是李家石匠的规矩,为防血脉混淆,会在自己牙齿上刻姓氏。
爷爷的臼齿上就有一模一样的刻痕,可爷爷从没说过,李家有同行死在这山里。
父亲的心沉到了谷底,他摸出石匠印章,印章上的莲花纹与玉佩纹路重叠,
在灯光下泛着幽幽绿光。突然,玉佩和印章同时发烫,骸骨的手指竟微微动了一下,
指骨指向黑洞的方向。父亲如梦游般直起身,高一脚浅一脚地向隧道走去。我见状,
急忙上前拉住他,高升说:“爸,累了一天了,今天先休息吧,有什么明天再说。
”父亲如大梦初醒般,顺着我的力道,跟我回到帐篷躺下。当晚,我躺在帐篷里,
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小张和老刘昏迷前的诡异状态、黑洞里的恶臭、洞口的神秘符号,
还有父亲反常的举动,像一团乱麻缠在我心头。迷迷糊糊间,
我似乎听到帐篷外有轻微的脚步声,像是有人在来回徘徊。我悄悄起身,
掀开帐篷的一角往外看。月光下,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朝着存放骸骨的临时棚屋走去,
正是赵队。他的动作很轻,像是在刻意躲避岗哨,手里还拿着一个手电筒,
光线被他用手帕裹着,只露出一点点微弱的光晕。一种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,
我立刻叫醒了身边的父亲。“爸,队长不对劲,他偷偷去棚屋了!”父亲闻言,
立刻警惕起来。他迅速穿好衣服,从床底下摸出一把防身的短刀,对我低声说:“跟我来,
别出声。”我们借着帐篷的阴影,小心翼翼地跟在赵队身后。只见他走到棚屋门口,
左右看了看,确认没人后,用钥匙打开了门锁,闪身走了进去。父亲示意我在门口守着,
自己则贴着墙壁,屏住呼吸听着里面的动静。过了没多久,棚屋里传来赵队的声音,
像是在打电话,语气恭敬又急切:“老板,他们已经发现黑洞了,
还挖出了一具骸骨……您放心,我已经按您的吩咐,让两个人暂时昏迷了,接下来该怎么做?
”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,赵队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:“现在就动手?
可是李铁山很警惕,而且工人们都盯着……好,我知道了,我会想办法的。”挂了电话,
赵队又在棚屋里停留了一会儿,似乎在检查骸骨。我和父亲大气不敢出,直到他离开棚屋,
朝着自己的帐篷走去,我们才悄悄退了回来。“看来,他果然和这件事脱不了干系。
”回到帐篷里,父亲的脸色异常凝重,“而且他背后还有人指使,目标就是那两块玉佩。
”“那我们现在怎么办?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其他工人?”我有些着急地问。“不行。
”父亲摇了摇头,“现在还不知道谁是赵队的亲信,贸然声张,只会打草惊蛇。
我们必须先找到证据,弄清楚他的真实目的。”他沉思了片刻,
眼神变得坚定起来:“明天赵队要到指挥部去汇报情况,当天晚上可能回不来,
我们要趁这个时候,去他的帐篷里找找,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他那本工作日志,
肯定藏着不少秘密。4. 第二天傍晚,赵队,我跟着父亲潜入队长帐篷时,
夜色已浓得化不开。营地的煤油灯大多熄灭了,只有远处的岗哨还亮着一点微弱的光,
风吹过帐篷的帆布,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响,像是有人在暗处窃窃私语。“动作轻点,
别弄出声音。”父亲压低声音,从帐篷的缝隙里观察着里面的动静。父亲示意我在门口望风,
自己则轻轻掀开帐篷的门帘,像一道影子般闪了进去。我紧握着拳头,心脏“怦怦”直跳,
耳朵警惕地听着周围的动静。山里的夜虫在不停鸣叫,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野兽的嘶吼,
每一点声响都让我神经紧绷。大约过了一盏茶的功夫,父亲从帐篷里钻了出来,
手里多了一个带锁的木盒。“走,回我们的帐篷再说。”父亲拉着我,快步回到自己的住处,
反手将帐篷门拉紧,又用背包顶住,用随身携带的工具,小心翼翼地撬开了锁。
木盒里除了那本泛黄的工作日志,还有一张旧照片和一封被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。
父亲飞快地抓起日志,借着煤油灯的光翻阅起来。日志本很旧,纸页已经变得脆弱,
一翻就掉渣,上面的字迹是用蓝黑墨水写的,有些地方已经褪色,需要仔细辨认。
前面的内容大多是筑路队的日常工作记录,比如推进的里程、材料的消耗、工人的考勤等等,
看起来平平无奇。可翻到中间的几页时,父亲的动作突然停住了,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
日志里写道:“今日在三号工作面施工时,发现一处天然溶洞,洞内有不明符号及人类骸骨。
带队组长陈石爷爷师弟的名字坚持进入探查,后溶洞突然塌方,陈石失踪,搜救无果,
上报为意外事故。”父亲拿起照片,只见照片上有两个年轻男人,
并肩站在一条刚开凿好的隧道口,笑容灿烂。其中一个男人,眉眼间和父亲有几分相似,
正是年轻时的爷爷,爷爷站着的那个精瘦男人,虽然面容陌生,但他们手里拿着的玉佩,
和我们从骸骨上取下的那块一模一样。背景的岩壁上刻着和如今黑洞边缘一模一样的符号。
最诡异的是,这张老照片没有褪色,反而像新拍的一样,用手摸上去,
符号的位置竟是温热的,照片里的玉佩还在微微发光,映得爷爷的眼睛格外明亮。
“这个男人,应该就是爷爷的师弟陈石。”父亲喃喃自语,又拿起那封信。
信是爷爷写给赵队的,内容很短,却信息量巨大:“陈石已入封印之地,玉佩分置两地,
方可保隧道安宁。切记,不可贪念宝藏,不可释放石灵,否则后患无穷。
若遇我后人持另一块玉佩而来,需助其完成守护之责,万不可心生歹念。”看到这里,
父亲终于明白了爷爷的良苦用心,也终于知道了赵队的背叛——他不仅没有遵守爷爷的嘱托,
反而勾结外人,妄图夺取宝藏,释放石灵。“不对,这里有问题。”父亲指着日志上的文字,
眉头紧锁,“爷爷说过,他师弟是个谨慎的人,绝不会贸然进入未知的溶洞。
而且‘天然溶洞’?我们发现的黑洞明明是人工开凿的,这两者根本对不上。
”我也觉得奇怪,忍不住说道:“会不会是队长记错了?或者当时的情况太混乱,记录有误?
”“不可能。”父亲摇了摇头,“赵队是出了名的细心,做记录从来不会出错。他这么写,
一定是在刻意隐瞒什么。”就在父亲准备将日志、照片和信收好时,
帐篷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。他来不及将东西放进箱子,人就已经走进来了。父亲反应极快,
立刻将笔记本塞进床板下的缝隙里,又用被褥盖住,熄灭了煤油灯。“李组长,你在吗?
”是队长赵队的声音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。父亲定了定神,拉开帐篷门,
装作刚被吵醒的样子:“赵队长?这么晚了,有什么事吗?”赵队站在帐篷门口,
手里拿着一盏煤油灯,灯光照在他脸上,表情有些复杂:“没什么大事,就是刚才醒来,
发现我的工作日志不见了,想着会不会是不小心掉在外面了,过来问问你有没有看到。
”父亲的眼神平静无波:“工作日志?没看到啊。会不会是你自己放忘了地方?
要不你再回去找找?”赵队盯着父亲的眼睛看了几秒,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,
可最终还是点了点头:“可能吧。打扰你休息了,抱歉。”说完,他转身离开了,
但我注意到,他走的时候,脚步有些犹豫,而且特意看了一眼我们帐篷的四周。
等赵队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后,父亲才重新点燃煤油灯,从床板下拿出笔记本。
“他已经怀疑我们了。”父亲的语气有些凝重,“我们必须尽快弄清楚真相。
”他继续往下翻,终于在笔记本的最后几页,找到了一段用铅笔写的补充记录,字迹潦草,
似乎是仓促间写下的:“溶洞并非天然,是人为开凿的封印之地。陈石并非意外失踪,
是他想释放洞内的‘石灵’,被我们阻止后,自愿留在洞内加固封印。玉佩有两块,
一块在陈石身上,一块在李山爷爷的名字身上,互为呼应,方能镇住石灵。
此事绝不能外泄,否则会引发大乱。”“原来是这样!”父亲恍然大悟,“爷爷一直隐瞒的,
就是这件事!赵队当年也是参与者,所以他看到你身上的玉佩时,才会那么紧张。
”就在这时,帐篷门被猛地推开,赵队带着两个亲信走了进来,手里还拿着木棍。“李铁山,
你果然看过我的日志了!”赵队的脸色阴沉得可怕,“既然你都知道了,那我也就不瞒你了。
”父亲站起身,挡在我身前:“你想干什么?”“既然你看见了,我就不瞒你了。
”赵奎叹了口气,把木棍扔在地上,“我是二十年前那队施工队的幸存者,你爷爷是我师父,
也是这一带最后的‘镇煞石匠’。”赵奎说,当年失踪的是爷爷的师弟,照片上的男人。
“你爷爷是石匠领头人,还懂‘镇煞’的手艺,他师弟心术不正,想放‘煞’挖古墓,
被你爷爷阻止了。那黑洞里的骸骨,根本不是他——是被‘煞’附了身的人。
”“那是谁的骨头?”父亲追问。赵奎突然打了个寒颤,
眼神里满是恐惧:“不知道……你爷爷当年只说,那是‘煞的容器’,必须封在里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