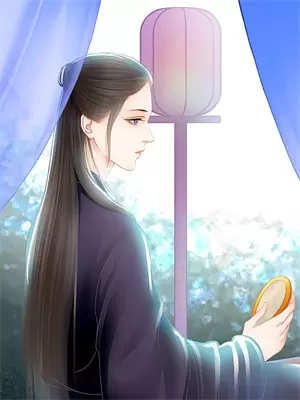有些东西丢了,就好像从来没存在过。比如童年弹珠,比如某次搬家时忘在抽屉里的旧照片。
它们无声无息地消失,在记忆里留下一个浅浅的坑,时间一长,风一吹,也就填平了。
也有些东西丢了,就像在你的生活里活生生挖掉一块肉。比如钥匙,比如钱包,
比如一份等着救命的合同。它会疼,会让你坐立不安,逼着你把整个世界翻个底朝天。
我叫陆闻声,是个做模型的。对我来说,丢东西就是要命的事。我所有的生活,所有的收入,
都系在一件件通过快递送到我手里的零件上。它们是我的骨,我的肉。可最近,我的骨肉,
一直在丢。不是一件,是每一件。起初我以为是意外,后来觉得是倒霉,现在我确定,
是有个天杀的贼,在小区的快递柜里,精准地掏空我的生活。今天,他又来光顾了。这一次,
他拿走的是我的命。我站在空荡荡的快递柜前,
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、黄得像烧给死人纸钱的信。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小字,
带着一股子陈年木头和香灰混合的怪味。“你好,我是忘川渡物流部的渡物使,
白小冉……”第 1 章我叫陆闻声。第三次站在小区的快递柜前。
金属柜门上又多了一道凹痕。那道凹痕和我脚上这只穿了三年的运动鞋鞋底纹路,完全吻合。
我伸出手,指尖在冰凉的触摸屏上一下一下地点着。输入提货码。屏幕绿光一闪,
跳出“提货成功”四个字。“啪嗒。”13号柜门应声弹开一条小缝。我的心,
跟着这声轻响,一直沉了下去。沉到了底。我拉开柜门。里面空空如也。
没有我等了半个月的“赤瞳”树脂改件。那个东西,巴掌大小,值三千块。有了它,
我才能完成手上这个尾款两万的订单。没有它,我下个月的房租,还有下个月的泡面,
就都没了着落。柜子里只有一股铁锈和灰尘混合的味道。呛人。我面无表情地关上柜门。
退后两步,右脚向后蓄力,准备给它再添一道新的凹痕。就在鞋尖快要碰到柜门的那一刹那,
我停住了。我的眼睛,看见13号柜门的内侧,好像粘着一张纸。一张黄色的纸。这不对劲。
那些塞小广告的,从来不会这么客气,还给你塞到柜子里面去。我压下火气,重新拉开柜门。
伸手,把那张纸扯了下来。纸不是普通的广告传单。它的质地很粗糙,泛着黄,
像是以前乡下糊窗户用的那种草纸。摸在手里,又轻又脆,好像稍微一用力就会碎掉。
纸上是用毛笔写的字。墨迹看上去很新,好像刚写上去没多久。“陆闻声先生亲启”。
字写得挺秀气,就是有点歪歪扭扭,一笔一划都透着一股子慌张。我把纸翻过来。
后面是几行小字。“你好,我是忘川渡物流部的渡物使,白小冉。
关于近期连续错拿您快递的事情,我司深表歉意……”我愣住了。忘川渡?
这是什么新开的快递公司?还渡物使?这又是什么新潮的岗位称呼?
听着跟古代摆渡的船夫似的。我往下看。“……因我司业务调整,系统出现短暂漏洞,
导致部分阳间货品被错误归档至‘无主之物’名录,并转运至地府仓。经查,
您于过去一月内丢失的共计十一件快递,均系我司渡物使白小冉即本人操作失误所致。
”信写到这,好像还用袖子擦过。有一小片墨迹晕开了,像一滴眼泪。“为表歉意,
我司特赔付《往来邮单》一册。
您可在邮单上写下任何您‘失去’的物品实体或概念皆可,投入阳间任意邮筒。
三日之内,该物品便会失而复得。此邮单亦可反向使用,将阳间之物寄往阴间,
邮费将从您的阳寿中自动抵扣,请谨慎使用。”“再次为给您带来的不便致歉。
祝您生活愉快,长命百岁。”落款是:手忙脚乱的渡物使,白小冉。
后面还画了个小小的、哭丧着脸的简笔画头像。我拿着这张信纸,站在快递柜前,半天没动。
风一吹,那纸边儿“哗啦啦”地响。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。恶作剧?谁会花这么大功夫,
偷走我十几个、总价值上万的快递,就为了跟我开这么一个不着边际的玩笑?
可如果不是恶作剧,难道是真的?地府?
快递员把我的模型零件当成无主孤魂给收到阴间去了?这比恶作剧听起来更像个笑话。
我把信纸折好,揣进兜里。一摸,兜里还真有个硬邦邦的小册子。我掏出来一看。
一本巴掌大的小本子,封面也是那种黄草纸,上面用同样的毛笔字写着《往来邮单》四个字。
翻开来,里面是一沓一沓更小的、裁切好的空白邮单。纸质和信纸一模一样。
每一张邮单上都印着简单的表格:寄件人,收件人,货品,备注。我的脑子很乱。愤怒,
绝望,还有一丝荒唐。客户的催款消息还在手机里闪。银行卡的余额红得刺眼。
房东下周就要来收租。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手里死死地攥着那本《往来邮单》。
路过小区门口那个绿色的、油漆都快掉光了的邮筒时,我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脚步。
我靠在邮筒上,从兜里掏出一支笔。那是一支我平时用来给模型画墨线的勾线笔,
笔尖细得像针。我撕下一张邮单,趴在邮筒顶上,开始写字。一股邪火顶着我的脑门。
去他妈的。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在“货品”那一栏,用尽全身力气,
一笔一划地写下:被偷走的所有模型零件。写完,我把那张轻飘飘的纸条揉成一团,
从邮筒那个生了锈的投信口里,塞了进去。纸团掉下去,发出“咚”的一声轻响。
像是掉进了一口很深很深的井里。第 2 章我一夜没睡好。或者说,我根本就没睡。
我坐在我的工作台前,台灯开着,照亮了一片狼藉。切割垫上散落着没用的流道,
工具架上的笔刀和镊子胡乱插着,空气里全是模型胶水和稀释剂的味道。
这是一个模型师的战场。只是现在,将军没了兵器。桌子中央,
那个半完工的模型静静地立着。那是一个1/6比例的机甲少女,客户要求极高,
每一个关节,每一片装甲,都必须打磨得完美无瑕。现在,它就像个被拆了骨头的病人,
右臂的接口空洞洞的,胸口的能量核心也是一个黑窟窿。它缺少的零件,
就是那个叫“赤瞳”的树脂改件,还有其他十个我为了这个订单准备的各种补品。
我盯着那个空洞,眼睛发酸。我把那封来自“地府”的信和那本《往来邮单》摆在旁边,
翻来覆去地看。越看越觉得荒唐。我一定是疯了。被逼疯了。居然会相信这种鬼话。
我开始盘算,现在去打零工还来不来得及。或者,把手头这些半成品便宜卖了?
还是干脆跟客户坦白,零件丢了,单子做不了,准备好被他骂个狗血淋头,
然后赔付三倍的定金。三倍定金。想到这个数字,我的胃就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。
天快亮的时候,我终于熬不住了,趴在工作台上睡了过去。我做了个梦。梦里,
我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邮筒里。邮筒下面不是箱底,而是一条浑浊的、流得很慢的河。
河上飘着各种各样的东西。有生锈的钥匙,有褪色的照片,有断了跟的旧皮鞋,
还有一些看不清形状、模模糊糊的光团。一个穿着古代邮差衣服的小姑娘,撑着一艘小船,
在河里捞东西。她一边捞,一边哭。“又捞错了,又捞错了……这个明明还有阳气,
怎么就下来了……”她抬头看见我,吓了一跳,手里的长杆一滑,差点掉进河里。
“你你你……你怎么也下来了?活人不能进忘川渡的!”我还没来得及说话,就醒了。
是被窗外透进来的光晃醒的。我抬起头,脖子僵得像块石头。眼睛也模糊。我揉了揉眼,
习惯性地看向我的工作台。然后,我整个人都定住了。我的工作台上,
那个半完工的机甲少女旁边,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堆东西。一个透明的塑料小盒,
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枚红色的、如同宝石般的机械眼球。是“赤瞳”改件。旁边,
是长谷川的水贴纸,郡仕的金属漆,wave的改造板,
田宫的打磨膏……所有我丢失的、总共十一件快递里的东西,一件不多,一件不少,
全都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。它们的包装盒上,还带着一点点潮气。
像是刚从某个很湿、很冷的地方拿出来一样。我伸出手,指尖颤抖着,
碰了碰那个装着“赤瞳”的盒子。是实体。冰凉的,坚硬的。不是幻觉。我猛地站起来,
椅子“咣当”一声被我带倒在地。我顾不上了。我冲到窗边,拉开窗帘。外面是清晨的阳光,
楼下有大爷在遛鸟,远处传来汽车的鸣笛声。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世界。我跑进厕所,
用冷水狠狠泼了一把脸。镜子里,是我那张写满了震惊和不敢相信的脸。我回到工作台前。
那些零件还在。它们真的回来了。我拿起那本《往来邮单》。它还是那个样子,
静静地躺在桌角,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撕下一张新的邮单。这一次,我的手不再发抖。
我坐在椅子上,想了很久。我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,我爸给我买过一台任天堂的GB游戏机,
黑白的,俄罗斯方块是我玩得最好的游戏。后来有一次搬家,
那台游戏机不知道被我塞到哪个箱子里,再也找不到了。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,拿起笔。
在“货品”那一栏,我写下了:童年时丢失的那台GB游戏机。我又把它揉成一团,
像昨天一样。出了门,我把它塞进了那个绿色的老邮筒里。“咚。”还是那声轻响。
像是有什么东西,掉进了另一个世界。第 3 章三天。信上说,三天之内,失物便会归还。
这三天,我过得像是在做梦。第一天,我用失而复得的零件,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
疯狂地赶工。我把“赤瞳”安装进机甲少女的眼眶,把断裂的机械臂接上,
给装甲喷上最后一层消光漆。我的手艺没有丢。当模型在我手中一点点变得完整时,
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专注,平静。好像之前所有的烦躁和绝望,
都被胶水和油漆的味道给覆盖了。我忘了《往来邮单》,忘了那个叫白小冉的冒失鬼渡物使,
忘了那个深不见底的邮筒。我只知道,我得先把眼前这个单子完成。这是我的本分。第二天,
我把完工的模型打包好,叫了最贵的闪送,发给了客户。一个小时后,手机震动。
客户发来一条消息。“牛逼!陆老师,尾款马上结!”紧接着,是银行的到账短信。
一串数字,让我紧绷了快一个月的神经,终于松弛了下来。我瘫在椅子上,
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活过来了。我点了个外卖,是楼下那家新疆菜馆的大盘鸡,
还奢侈地加了两份馕。我一边吃,一边看着窗外。天色渐渐暗下来,
城市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都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它太大,
太亮,太吵。我只是缩在顶楼这个小小的壳里,靠一双还算灵巧的手,
换一点能填饱肚子的食粮。但今天,我觉得这夜景还挺好看的。吃完饭,我收拾了桌子,
把所有的工具都擦拭干净,整整齐齐地放回工具架上。这是我的习惯,我的工作台可以乱,
但工具必须干净。做完这一切,已经是深夜。我坐在桌前,又一次拿起了那本《往生邮单》。
我突然想起,我前天还寄出了一张邮单。写的是我童年的那台GB游戏机。
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。会有用吗?找回模型零件,或许是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存在,
只是被“错拿”了。可一台丢失了快二十年的游戏机呢?它可能早就被当成垃圾处理掉了,
可能早就被拆解得不成样子了。这也能找回来?我心里没什么底。甚至觉得有点可笑。
自己是不是太贪心了?我站起来,准备去洗个澡睡觉。就在我转身的时候,我的眼角余光,
扫到了床底。我的床底下,平时是空的。我有点洁癖,不喜欢在床下堆东西。但现在,
床底下那个阴暗的角落里,好像有个方方正正的影子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我蹲下身,
凑过去看。那是一个灰色的,长方形的塑料盒子。上面有十字方向键,
有A、B两个红色的按钮,还有一块长方形的、如今看来小得可怜的黑白屏幕。
是GB游戏机。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。连左下角那个被我摔出来的小缺口,都还在老地方。
我伸手把它拿了出来。机身很冷,带着一股子……怎么说呢,
像是老衣柜里翻出来的旧衣服的味道。很陈旧,但并不脏。我按了一下电源开关。没反应。
应该是没电了。我翻箱倒柜,找出了四节五号电池。我记得这玩意儿用的是四节电池。
我把电池装进去,盖上后盖。深吸一口气,再次拨动了那个小小的电源开关。
“滴——”一声熟悉的电子音响起。黑色的“Nintendo”字样,
从屏幕上方缓缓落下。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热了。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。
是被地府的“快递员”从哪个世界的垃圾堆里翻出来的,
还是用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力量重新“组合”出来的。我只知道,我失去了二十年的东西,
现在又回到了我的手里。我坐在冰凉的地板上,借着台灯的光,玩了一晚上的俄罗斯方-块。
直到天亮,我才发现那本《往来邮单》下面,压着一张新的纸条。不是邮单。
是白小冉的回信。还是那手忙脚乱的字迹:“陆先生!您的‘订单’已送达!
那台游戏机可真难找,都快成古董啦!另外,上次您寄过来的‘愤怒’情绪我们已经处理了,
地府最近正好缺这个,用来给油锅加热,效果好极了!谢谢您的惠赠!”我愣住了。
我寄过去的,是那张写着被偷走的所有模型零件的邮单。我当时确实很愤怒。
原来……我寄过去的,不只是文字。还有我写下那些字时的情绪?
“邮费将从您的阳寿中自动抵扣。”我想起了信里的那句话。那我寄过去的“愤怒”,
抵扣了多少阳寿?我的后背,忽然有点发凉。第 4 章阳寿抵扣。这四个字,像一根小刺,
扎在了我心里。我开始有点害怕了。我得到的,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模型零件,游戏机。
那我付出的呢?“阳寿”这种东西,看不见,摸不着。它到底是怎么计算的?
我寄出了一团“愤怒”,用来给地府的油锅加热。这件事听起来很荒诞,但细想一下,
又让人毛骨悚然。这本《往来邮单》,不是一个许愿机。它是一个交易平台。
我把玩着手里的GB游戏机,它的外壳冰冷,塑料的质感很硬。可我总觉得,
这东西好像……有点不对劲。它太“新”了。虽然样子还是老样子,缺口也还在,
但它没有那种被岁月和人手反复摩挲过的温润感。它就像一个完美的复制品,
精确地复刻了所有的外观,却唯独没有复刻灵魂。我把它收进了抽屉里。再也没拿出来过。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我没再用过那本邮单。我接了新的订单,按部就班地采购零件,
制作模型。快递也再没有丢过。生活好像回到了正轨,除了我的桌子上,
始终放着那本黄色的、诡异的小册子。它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。
你知道里面装着能解决你一切烦恼的宝物,但也知道,打开它,
可能会放出你无法控制的魔鬼。我开始频繁地失眠。闭上眼睛,就是那条浑浊的忘川河,
和那个撑船捞东西的小姑娘。我总是在想,我到底被扣了多少“阳寿”?一天?一个月?
还是一年?这种未知的恐惧,比贫穷更折磨人。直到有一天,我下楼扔垃圾,
碰到了住在一楼的张大爷。张大爷七十多了,是个独居老人。老伴前几年走了。
他身体还算硬朗,就是记性越来越差。每天最大的乐趣,就是搬个小马扎,
坐在楼门口的树荫下,跟来来往往的邻居唠嗑。那天他看见我,招了招手。“小陆,
又去做模型啊?”“是啊,张大爷。”我笑着应了一声。他叹了口气,拍了拍自己的脑门。
“唉,我这脑子,越来越不中用了。昨天我闺女回来看我,
问我还记不记得我老伴儿年轻时候最喜欢穿哪件衣裳。我愣是想了半天,一点都想不起来了。
”他浑浊的眼睛里,透着一股子失落和茫然。“就记得她笑起来有两个酒窝,特别好看。
可她穿什么衣裳,梳什么辫子,我这脑子里,就跟蒙了一层雾一样,模模糊糊的,
怎么也看不清……”“就好像……把那段日子给弄丢了。”他说完,又叹了口气,
不再说话了。我站在他旁边,看着他布满皱纹的侧脸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,
在他身上落下一块一块的光斑。把日子给弄丢了。我心里某个地方,被这句话轻轻地触动了。
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。一个大胆的,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的念头。信上说,
邮单可以找回“实体或概念”。记忆,算不算一种“概念”?
如果……如果我能帮张大爷找回他对老伴的记忆呢?这个念头一出来,就怎么也压不下去了。
它像一棵疯狂生长的藤蔓,缠住了我的心脏。我不是为了我自己。
我是为了帮一个可怜的老人。我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。那天晚上,我鬼使神差地,
又撕下了一张邮单。我犹豫了很久。我害怕“阳寿抵扣”。
可我又想起了张大爷那双失落的眼睛。最终,我在“寄件人”那一栏,
写上了“一楼的张大爷”。在“货品”那一栏,
我写道:对已逝老伴年轻时最清晰的记忆。在“备注”里,我多加了一句:邮费由我,
陆闻声,承担。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。我甚至不知道,我有没有资格替别人“下单”,
又有没有资格替别人“支付”。我把这张邮单投进了那个绿色的邮筒。这一次,
我没有听到“咚”的一声。邮筒里,静悄悄的。第 5 章第二天,什么也没发生。第三天,
也什么都没发生。张大爷还是每天坐在楼门口,唉声叹气,说自己脑子不管用了。
我心里有点失落,又有点庆幸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,
果然不是一本小册子就能找回来的。也好,至少我的“阳寿”保住了。
我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,继续做我的模型。大概过了一个星期。那天我下楼买东西,
又看到张大爷坐在老地方。不同的是,他今天没发呆,手里拿着一个相框,
正用一块布小心翼翼地擦着。他的表情,是我从未见过的。专注,温柔,
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。我好奇地凑了过去。“张大爷,看什么呢?”他抬起头,看到是我,
眼睛一亮。“小陆,你来看!”他把相框递给我。那是一张很老的黑白照片。
照片已经泛黄了,但保存得很好。照片上,是一个很清秀的姑娘,梳着两条大辫子,
穿着一件的确良的碎花衬衫,靠在一棵大树下,笑得很甜。两个浅浅的酒窝,清晰可见。
“这是……师母年轻的时候?”我问。“是啊!”张大爷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得意。
“好看吧!我就说我记得嘛,她年轻时候最喜欢穿这件碎花衬衫了!我前两天收拾老箱子,
就从箱子底把它给翻出来了。你说怪不怪,我之前怎么也想不起来,一看到这张照片,
一下子就全想起来了!”我的手,拿着那个相框,微微有些发抖。这个相框,
我从没见张大爷拿出来过。而且,这照片也太新了。虽然是黑白泛黄的色调,但纸张的质感,
相纸的边缘,都像是最近才冲印出来的。“真好啊。”我把相框还给他,声音有点干。
“可不是嘛!”张大爷宝贝似的把相框抱在怀里,“有了它,我就不怕以后把她忘了。
”我跟张大爷道了别,恍恍惚惚地往外走。所以……邮单起作用了。
它没有直接把“记忆”塞回张大爷的脑子里。而是用一种更巧妙,
更符合这个世界逻辑的方式——它“创造”了一张照片。一张承载着那段记忆的照片,
让它以一个合理的姿态,出现在张大爷的生活里。失而复得。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有种奇异的满足感,也有一种更深的寒意。这种力量,太可怕了。它不只是“寻找”,
它甚至可以“创造”。那天晚上,我又收到了白小冉的回信。
纸条是夹在我新买的一瓶模型漆的盖子里的。“陆先生,您真是个好人!
您寄来的那份‘记忆’,我们已经收到了。它被转化成了一段很温暖的光,
用来照亮奈何桥了。过桥的魂魄们都说,感觉心里暖洋洋的。作为感谢,
这次的邮费给您打了八折哦!”八折……我苦笑了一下。也就是说,还是扣了。信的末尾,
还有一行小字。“对了,陆先生。我叫白小冉。是地府忘川渡部门的新人……我,
我们能通过邮单,交个朋友吗?我在地府……一个朋友都没有。”字迹写到最后,有点抖。
一个在地府工作、没有朋友的、冒失的渡物使。我对着这张纸条,愣了很久。我回了信。
我找了一张新的邮单,在上面写道:“你好,白小冉。我叫陆闻声。是个做模型的。
很高兴认识你。”我把它投进了邮筒。从那天起,我和这个来自阴间的“笔友”,
开始了一种奇特的交流。她会告诉我一些地府的趣闻。比如孟婆汤最近出了新口味,
是香草味的。比如牛头马面因为谁的业绩更好吵了一架。
比如她今天又差点把一个要投胎的魂魄错送到畜生道。我也会跟她讲一些阳间的事情。
比如我今天做的模型有多复杂,楼下的猫又生了一窝小猫,今天的天气很好。我们的信件,
通过那个绿色的邮筒,往来于阴阳两界。我渐渐觉得,这个《往来邮单》,
或许不是什么魔鬼的契约。它也可以很温暖。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念头。或许,
我能用它来做更多的好事。帮助更多像张大爷一样,“弄丢了”宝贵东西的人。我开始觉得,
自己不再是那个缩在壳里的孤独模型师了。我成了一个“信使”,一个连接着两个世界,
能为人弥补遗憾的特殊存在。这种感觉,很好。直到那封血红色的信到来。
第 6 章那封信来得很突然。那天我正在给一个高达模型做旧化处理,用棉签沾着渍洗液,
小心地擦拭着模型的边缘。一阵冷风,毫无征兆地从我紧闭的窗户缝里钻了进来。风不大,
却吹得我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我手里的棉签“啪嗒”一声掉在桌上。我看到,
原本放在桌角的《往来邮单》,无风自动,自己翻开了一页。一封信,从册子里飘了出来,
落在我面前。信纸不再是那种泛黄的草纸。它是一种惨白色,
纸上还带着斑斑点点的、像是血迹一样的暗红色。上面的字迹,
不再是白小冉那种娟秀又慌张的字体。而是用一种更加潦草、更加用力的笔迹写成的。
每一个笔画,都透着一股子绝望和惊恐。“陆闻声!救我!!”开头就是这四个字。
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喊出来的。“我弄丢了!我把一件最重要的‘货品’弄丢了!
那不是普通的‘无主之物’,那是一个刚离世的女孩的魂魄!她叫季安歌,
本来是要被送到一个很重要的、我不能说的地方去的!”“她跑了!就在我交接的时候,
她从我手里跑了!如果找不回来,按照忘川渡的规矩,我……我会被打得魂飞魄散的!
”“陆闻声,我没有办法了!地府的追捕队找不到她,她好像用了什么法子,
把自己在阴间的气息全都隐藏起来了。但她一定还在阳间!她还有执念未了!”“求求你!
求求你在阳间帮我找找她!只有你能感觉到她!因为你的身上,有我们忘川渡的气息!
”“只要你能帮我找到她,我就……我就去求我的主管,
把那张整个地府只有一张的‘特许万能邮单’给你!那张邮单,
可以让你换回任何你想要的东西!任何东西!”“求求你!我不想魂飞魄散!
我还想……还想和你通信……”信的最后,是一个用暗红色画出来的、巨大的哭脸。那颜色,
深得像真的血。我拿着这封信,手心全是冷汗。魂魄。这次不是模型零件,不是游戏机,
也不是一段记忆。是一个人的魂魄。季安歌。这个名字,像一块冰,砸进了我的脑子里。
我感觉事情开始失控了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一个做模型的。我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
可现在,我却被卷进了一件关乎一个“渡物使”生死存亡,
甚至还牵扯到一个陌生魂魄的大麻烦里。我该怎么办?拒绝她?
然后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和我通过信、会告诉我孟婆汤新口味的冒失鬼姑娘,魂飞-魄散?
我做不到。我的脑子里,浮现出她那手忙脚乱的字迹,和那个总是画在信尾的、小小的哭脸。
我没见过她。但我感觉,我已经把她当成了朋友。一个很特别的,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朋友。
我不能见死不救。还有那个“特许万能邮单”。可以换回“任何东西”。这句话,
像一个魔咒,在我耳边盘旋。人的欲望是无穷的。当我拥有了可以找回小物件的能力后,
我就开始渴望能弥补更大的遗憾。如果,我拥有了可以换回“任何东西”的能力呢?
我能用它来做什么?我深吸一口气,从《往来邮单》里,撕下了一张空白的邮单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找一个魂魄。但我别无选择。我在“货品”那一栏,
写下了季安歌魂魄的踪迹。这一次,我没有在备注里写“邮费由我承担”。因为我知道,
从我写下这行字开始,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这场交易的代价,恐怕会大到我无法想象。
我把邮单投进邮筒。这一次,邮筒里传来的,不是“咚”的一声。而是一声若有若无的,
女人的叹息。第 7 章邮单投进去的瞬间,我的世界变了。不是天翻地覆的那种变。
是一种更细微,更诡异的变化。我的眼睛,好像多了一层滤镜。周围的一切,
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老旧的楼房,喧嚣的街道,来来往往的行人。但是,在这些实体之间,
我开始能看到一些别的东西。一些淡淡的、像是水汽一样的影子。它们有的聚成一团,
停留在某个地方。比如街角的垃圾桶旁,有一团灰色的、带着“懊悔”情绪的影子,
我猜那可能是某个人扔掉彩票后留下的。医院门口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