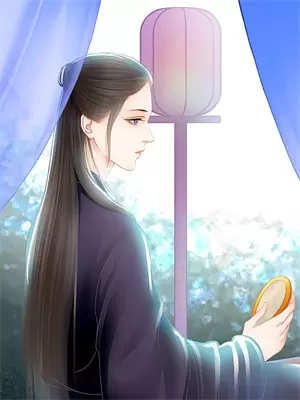我叫萧然,职业是给城市“降噪”的。但我的世界,却是全天下最吵的。一年前,
一场实验室事故,让我能听见一种正常人无法感知的“耳语”,一种能把人逼疯的高频噪音。
我被当成疯子关了整整一年,才学会假装自己听不见。出院后,我只想当个普通人,挣钱,
吃饭,活下去。直到我遇见孟遥。她正优雅地介绍着她的香水,我却看见她白皙的耳廓,
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。那一刻,我脑子里海啸般的“耳语”告诉我——完了,
她也“听”到了。她是我见过唯一一个,能听见我世界里噪音的人。
1我的人生信条是:保持低调,远离麻烦,活得像个背景板。
但当我第一次在“浮光”集团的香氛发布会上见到孟遥时,
我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“正常人”伪装,碎了一地。她站在台上,
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白色长裙,像一株在月光下悄然绽放的白玉兰。她就是孟遥,
这次发布会的主角,一位天才调香师。“这款‘月下之影’,我想表达的,
是一种在绝对静谧中,才能被感知的生命力……”她的声音清冷又温柔,像山涧里的溪水。
台下的精英们听得如痴如醉。而我,作为被客户请来评估会场声学环境的声景设计师,
却像个坐立不安的贼。我的注意力根本不在什么混响和分贝上,而是死死地盯着她。
就在她举起那瓶设计得像一弯新月的香水时,动作优雅,手腕纤细。灯光下,
她白皙剔透的耳廓,微不可察地颤动了一下。就是那一下。
仿佛有人在我脑子里引爆了一颗深水炸弹。嗡——!那该死的、只有我能听见的“耳语”,
瞬间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滔天巨浪,几乎要把我的头盖骨掀开!我猛地攥紧拳头,
指甲深深嵌进掌心,用疼痛来对抗这股疯狂的音波。我敢用我仅有的一切打赌,
她“听”到了。这玩意儿根本不是什么狗屁“幻听”。我给它起了个名字,叫“回音”。
一年前,我还在穹顶集团的声学实验室工作。那是个披着科技公司外衣的怪物,
背地里在研发一种通过次声波影响人类情绪的武器。一次该死的事故,设备失控,
泄露的能量场把我的听觉系统给永久性地“格式化”了。从那天起,
我成了唯一能听到那场事故“回音”的人。这“回音”就像一种精神病毒,
会慢慢侵蚀正常人的潜意识,诱发焦虑、偏执,最后把一个活生生的人,
变成一个只会对着空气尖叫的疯子。我就是第一个受害者。而孟遥,我死死盯着她。
她的资料我看过,万里挑一的嗅觉天才,能分辨上千种气味分子。这种人,
神经系统天生就比普通人敏感百倍。她那对气味的极致敏感,
无意中也让她的听觉变得异常敏锐。她成了下一个完美的“易感者”。
她开始能捕捉到“回音”的边缘信号了。2我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万个念头,
又被自己一一否决。报警?跟警察说,嘿,
有一种你们谁也听不见的声音正在追杀一个美女调香师,
而我是唯一能听见这声音的“先知”?
他们会客气地把我请回一年前我待过的那个精神康复中心,顺便给我来一针大剂量的镇定剂。
穹顶集团的势力有多大,我比谁都清楚。他们能把一场致命的实验室事故,
粉饰成一次“设备常规维护”,能把一个前途无量的研究员,
悄无声息地定义为“精神分裂”。他们只会把我当成一个还没治好的疯子,
一个随时可能泄露秘密的麻烦。那直接告诉孟遥?我都能想象出那个画面了。我冲上去,
抓住她的手,用一种自以为深沉又急切的语气说:“孟小姐,
你正在被一种看不见的声音追杀,只有我能救你!”最好的结果,是她礼貌地叫保安。
最坏的结果,是我因为骚扰女性,当天晚上就登上社会新闻,
标题大概是《变态设计师发布会现场搭讪天才调香师,言语惊悚疑似精神失常》。
我颓然地靠在会场冰冷的墙壁上,看着台上光芒万丈的孟遥,她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一无所知。
而台下,衣冠楚楚的人群里,说不定就混着穹顶集团的眼睛。他们在寻找,
寻找像孟遥这样的“样本”,来验证他们那杀人不见血的武器。不行。
我不能让她被那群混蛋发现。在她被“回音”彻底吞噬之前,在她被穹顶集团的人盯上之前,
我必须做点什么。常规的、正常的、合乎逻辑的方式,全都行不通。我的身份,我的经历,
让我在这件事里,天然就处于一个“不可信”的位置。那就只能用不正常的方式了。
一个疯狂的念头,像藤蔓一样从我心底最阴暗的角落里滋生出来,迅速缠绕住我的理智。
既然无法让她相信我,那就让她“需要”我。既然无法光明正大地保护她,
那就把她拽进我为她打造的“安全区”。我要用我的方式,在她的世界里无孔不入,
让她在不知不觉中,彻底依赖上我为她构建的“静谧”。我要“追”到她。用一种最直接,
也最变态,最疯狂的方式。3计划一旦成型,我的行动力就变得极其恐怖。
我的人生信条被揉成一团,扔进了垃圾桶。现在,我只有一个目标:占有孟遥的世界,
或者说,保护她。我没去买玫瑰,也没预定什么米其林餐厅。我花光了积蓄,
从黑市搞来了一批昂贵的铅制隔音毡,又熬了三个通宵,用实验室里偷出来的零件,
攒出来一个巴掌大的金属盒子——我管它叫“谐波抵消器”。
这玩意儿能发出一种微弱的、特定频率的白噪音,像一道防火墙,把“回音”隔绝在外。
接下来的行动,让我自己都觉得像个变态。我花了三天时间,摸清了孟遥的作息规律。
她独居,在一个安保严格的高档小区。安保严格?对我这种专业人士来说,
不过是多花点时间的问题。在一个她外出工作的下午,我像个幽灵一样,溜进了她的公寓。
房子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、清雅的香味,是她身上的味道。我没有时间分心,直奔她的卧室。
那是我为她选择的第一个“安全区”。我撬开墙板,
小心翼翼地将铅制隔音毡一层层铺设进去,再重新封好,处理得天衣无缝。最后,
我把那个造型古怪的“谐波抵消器”藏在了她床头柜后面,连接上电源。做完这一切,
我像蒸发了一样离开,没留下一根头发丝。我的“礼物”送到了。很快,
孟遥的世界开始出现“怪事”。这是我通过一些特殊渠道“听”说的。
她先是觉得自己的卧室好像安静得过分了,那种城市背景里若有若无的嗡鸣消失了。接着,
她偶尔会在夜深人静时,
墙壁里传来一阵极其微弱的、像是电流流过的嗡嗡声——那是“谐波抵消器”在工作的声音。
最让她毛骨悚然的,是某天早上醒来,她发现床头柜后面,
多了一个她从没见过的、银灰色的金属盒子。上面没有商标,没有按钮,只有几道散热格栅,
摸上去还有点温热。她吓坏了,以为家里进了贼,或者更糟——闹鬼。
她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,什么都没少。她叫来了物业,带着专业的设备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,
电工说线路没问题,保安说监控没异常。那个金属盒子,
被物业当成某种新型的香薰机或者驱鼠器,拿去研究了半天,也没搞懂是什么。最后,
只能不了了之。孟遥彻底陷入了困惑和恐惧。她不知道,在她看不见的地方,
我正通过一个微型摄像头,看着她在自己家里疑神疑鬼,看着她紧锁眉头,
看着她眼底的惊恐。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。但这是必须的。这是我送她的第一份“守护”,
一份她无法理解的守护。4孟遥的生活,被我亲手推向了失控的边缘。而我,这个始作俑者,
却只能躲在暗处,扮演一个冷酷的上帝。我黑进了她的社交软件和日程表,
对她的所有安排了如指掌。很快,我发现一个叫林嘉文的青年才俊正在追她。金融新贵,
长得人模狗样,出手也大方。他约孟遥去一家顶楼的旋转餐厅吃饭。我看到地址的瞬间,
后背就窜起一股凉气。那地方是A市的地标建筑,顶楼三百六十度无遮挡,
简直就是城市声波的露天交汇点,“回音”的天然大喇叭。让孟遥去那里,
跟把一只兔子扔进狼窝没区别。我不能让她去。约会当晚,
我坐在自己那堆满了各种仪器的出租屋里,像个指挥中心的调度员。面前的屏幕上,
一个是餐厅的公共监控画面,另一个是我编写的触发程序。监控里,
林嘉文殷勤地为孟遥拉开椅子,孟遥礼貌地微笑。餐厅缓缓旋转,
城市的璀璨夜景在他们身后流淌。美得像一幅画。但我知道,在那片璀璨之下,
致命的“回音”正在汇集。我通过随身携带的简易频谱仪的远程数据看到,
代表“回音”的波峰在急剧攀升。屏幕上,孟遥的笑容开始变得有些勉强。
她不自觉地用手指揉了揉太阳穴。时候到了。我深吸一口气,按下了回车键。下一秒,
餐厅里响起了刺耳的火警警报!红灯爆闪,喷淋系统开始洒下水雾。食客们尖叫着,
乱作一团。我看到林嘉文手忙脚乱地护着孟遥,而孟遥,她捂着头,脸色惨白,眼神涣散。
在混乱的人群中,她那痛苦的表情,像一把刀子狠狠扎进我的心脏。她不是因为火警而痛苦,
她是因为“回音”的猛烈冲击。警报声虽然刺耳,
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并干扰了“回音”的频率,反而救了她。这场“浪漫”的约会,
就在一片鸡飞狗跳中狼狈收场。孟遥以为只是倒霉。但很快,她就发现,
这种“倒霉”如影随形。她和林嘉文约好去看一场备受期待的歌剧,开场前五分钟,
剧院因为“线路检修”突然宣布取消演出。他们改去一家新开的酒吧,刚坐下,
就遇上“煤气管道泄漏”,整条街紧急疏散。一次是巧合,两次是倒霉,
三次、四次……孟遥不是傻子。她开始怀疑,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故意搞鬼,故意针对她。
她看林嘉文的眼神,也从最开始的礼貌,多了一丝审视和怀疑。很好,我的目的达到了。
但看着她越来越憔悴,眼底的惊惶和不安越来越浓,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5我的疯狂追求,
终于引来了孟遥最激烈的反弹。她没爱上我,也没依赖上我,
她把我当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变态跟踪狂。我开始尝试更“温和”的方式。
我根据“谐波抵消器”的原理,调配了一种特殊的香薰精油,
里面混合了几种能暂时屏蔽神经信号传导的罕见植物成分。这东西能让她睡个好觉。
我捧着包装精美的香薰,等在她公司楼下。这是我第一次,
试图以一个“正常追求者”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。下午六点,她走了出来,
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,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。当她看到我时,先是愣了一下,随即,
那双漂亮的眼睛里,瞬间充满了警惕和厌恶。“孟小姐。”我走上前,声音有些干涩。
“是你?”她的声音比十二月的冰还冷,“你到底想干什么?
”“我……”我把手里的香薰递过去,“这个……能帮助睡眠,没有副作用。
”她看了一眼那个盒子,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。她没有接,只是冷冷地看着我,
眼神像刀子一样。“之前那些事,是不是都是你干的?”我无法回答。我能说什么?
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你?她只会觉得我疯得更厉害了。我的沉默,在她看来就是默认。
“你真让我恶心。”她一字一句地说。然后,她抬手,狠狠一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