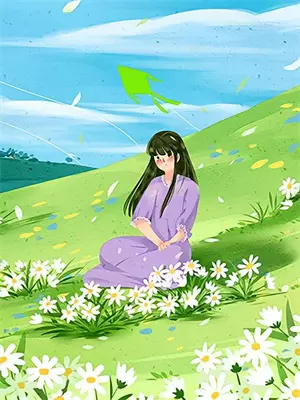消毒水刺鼻的气味在鼻尖萦绕不散,仿若一层寒霜,冻住了所有的温暖与希望。
林夏僵立在肿瘤科主任办公室外,紧紧攥着孕检报告,指尖因用力而泛白,
宛如冬日里被寒风肆虐的枯枝。透过那虚掩的门缝,
她望见程远舟白大褂的衣角在晨光中泛着冷调的青灰,这抹颜色瞬间勾起了他们初遇的回忆。
那是六年前的秋分,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,洒在胡同深处的咖啡馆里。
她正专注地用相机捕捉着生活的美好,却不慎将镜头撞在了程远舟端咖啡的手腕上,
卡布奇诺的奶泡在他浅灰毛衣袖口洇开,恰似一朵洁白的云。程远舟微微一怔,
随后弯腰捡起相机,他后颈凸起的脊椎骨在日光下折射出瓷器般的光泽,那一刻,
时间仿佛静止。“我是程远舟,肿瘤科医生。”他递出名片,手指修长而苍白,
虎口处那道月牙形的疤痕格外醒目。后来,在一个宁静的夜晚,
他向她诉说了这道疤痕的来历,那是他十六岁化疗时咬碎体温计留下的,
是他与死神抗争的印记。回忆渐渐淡去,林夏的小腹传来微微的抽痛,
思绪又被拉回到了现实。昨夜,程远舟提出离婚时,眼底涌动的暗潮让她感到陌生。
他总是这般,将医嘱般的冷静藏在温润的外表之下,连告别都如同宣读病理报告般冰冷。
“孕六周。”B超单在她掌心被揉得皱巴巴的,她的思绪飘到了上周。
他们在深夜急诊室相遇,他的白大褂上沾染着抢救病人的血迹,而她刚结束杂志社的拍摄。
消毒水与血腥气在更衣室里交织,发酵成一种酸涩的欲望,恰似他们聚少离多的婚姻,
总是在生死的缝隙中寻找着短暂的温暖。护士站的挂钟清脆地敲响了八下,打断了她的思绪。
程远舟转身的瞬间,林夏瞥见他左胸口袋露出的浅蓝纸角,那是肿瘤医院的检查报告。
她猛地想起三个月前的那个暴雨夜,他浑身湿透地回到家,称是为了抢救病人而淋雨。
可她分明看到他白大褂内袋里的病历单上印着“程远舟”三个字,
日期就在他们最后一次争吵之前。林夏踉跄地退到消防通道,
孕吐的酸水混合着泪水在喉咙里灼烧,令她痛苦不堪。
手机相册自动跳出回忆的画面:去年生日,
程远舟送她的星空投影仪在卧室天花板投下猎户座的光斑。他曾说,
在医学院解剖课最疲惫的时候,总会想起捐骨髓救他的那个女孩眼尾的泪痣,
“像天狼星落在雪地上”。此刻,她终于明白,那个雪夜他为何死死攥着捐髓同意书,
身体止不住地颤抖。当年那个十六岁的白血病少年,如今三十四岁的肿瘤科医生,
终究还是没能逃脱命运的捉弄。住院部三楼窗外的老槐树开始落叶,
金黄的叶片如一只只疲惫的蝴蝶,纷纷扬扬地扑落在程远舟空荡的办公桌上。
林夏轻抚着尚未隆起的小腹,想起昨夜他最后一次吻她时,唇间若有若无的铁锈味,
那是生命消逝的预兆,只是她未曾察觉。消毒水的气味不知何时被一股甜腥味取代,
林夏跪在血液科档案室,四周弥漫着陈旧纸张和岁月的气息。泛黄的捐髓登记表上,
“苏蘅”这个名字如同一根生锈的针,狠狠地刺进她的视网膜。2003年平安夜,
城市被节日的氛围包裹,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圣诞的欢愉,而在骨髓库的匹配通知里,
苏蘅第一次看到“程远舟”这个名字。彼时,
她刚凭借画作《化疗室的天窗》斩获全国美展金奖,站在领奖台上,镁光灯闪烁,
可她却咳出一口血沫,殷红的血迹在雪白的画纸上蔓延,触目惊心。
“他的HLA配型和我完全吻合。”十五岁的苏蘅,声音带着少年独有的青涩与坚定,
她轻轻将通知单折成纸船的模样,小心翼翼地放进白血病病房的洗手池。池子里,
漂白水味道的漩涡不断翻涌,在那混沌的水流中,她望见自己因激素治疗而浮肿的脸,
面庞圆润却毫无血色,与程远舟病例照片上那个清瘦阴郁的少年相比,
一个像被岁月磨损、布满锈迹的齿轮,一个则似崭新锃亮、等待运转的发条,
截然不同却又即将被命运紧紧缠绕。穿刺针扎进髂骨的那天,疼痛如汹涌的潮水般袭来,
苏蘅在镇痛泵制造的朦胧幻觉里,拿起画笔,凭着模糊的记忆画下程远舟的脊椎。
一旁的护士轻声说道,捐髓过程中,她一直在哼着《红河谷》,
那悠扬的旋律仿佛能驱散些许痛苦。然而,程远舟移植舱的监控录像却记录下了另一番景象,
少女苍白干裂的唇形,分明在无声地诉说:“要带着我的细胞去看海啊。”每一个字,
都像是在与命运抗争,又像是对未来的期许。2004年春天,万物复苏,
程远舟带着苏蘅给予的干细胞,重获新生,生命的活力再次在他体内涌动。
可苏蘅却陷入了排异反应的泥沼,不断下沉。当程远舟收到医学院录取通知书,
满心欢喜地开启新征程时,苏蘅正坐在病房里,用那因化疗而溃烂、布满创口的手指,
一点点往病房窗户上贴星图贴纸。她拿起口红,在玻璃上仔细地画出渤海湾的轮廓,
那片她心心念念的大海,可在潮汐最高的地方,她却用颤抖的手写下:“程远舟不会来”,
字迹歪歪扭扭,透着无尽的失落与孤独。“他每周都寄明信片。”护士悄悄来到苏蘅床边,
将盖着肿瘤医院邮戳的信件,轻轻塞进她的枕头下。程远舟用解剖图的背面画下星空,
每一颗星星都闪烁着他的思念。最新的那张上,
猎户座腰带上清晰地标着经纬度:东经121°47',北纬39°02',
正是苏蘅渴望前往的渤海坐标,那密密麻麻的数字,像是他跨越千山万水传递的牵挂。
2005年惊蛰,春雷隐隐,可苏蘅的身体却每况愈下,皮肤开始大片剥落,
生命的烛火在狂风中摇摇欲坠。她拼尽最后的力气,篡改病历,
写下“自愿停用免疫抑制剂”,那一笔一划,都是她对命运的抉择。深夜,
抢救室里灯火通明,仪器的滴答声、医生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。
她虚弱地扯过程远舟实习胸牌的挂绳,将沾着鲜血的素描本,塞进他颤抖的手中。
素描本的最后一页,画着一位穿婚纱的少女,亭亭玉立地站在海浪里,裙摆随风飘动,
上面用红蓝铅笔仔细标注着“CD34+细胞活性分布图” ,
那是她用生命谱写的浪漫与希望,也是她留给程远舟最后的礼物。
2003年的冬天在纸页上缓缓复苏,十五岁少女眼尾的泪痣被圆珠笔特意圈出,
捐献日期正是程远舟骨髓移植手术当天。林夏想起去年深秋,程远舟值完大夜班后突然发烧,
锁骨处浮现的出血点宛如散落的朱砂,那时的她并未意识到,这是命运再次敲响的警钟。
医院顶层的危重病房亮着幽蓝的灯光,仿佛一座被黑暗笼罩的孤岛。林夏贴着冰凉的玻璃,
看着程远舟的侧脸深陷在呼吸面罩里,输液架上挂着淡紫色的长春新碱。
他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松松垮垮,似乎随时都会滑落。“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,
Ph染色体阳性。”主治医师的声音被监护仪的嘈杂声切割得支离破碎,
“三年前复发时他拒绝第二疗程,说要把最后的时间留给......”话未说完,
却像一把重锤,狠狠地砸在林夏的心上。林夏的孕肚不小心撞在门框上,
十八周大的胎儿突然剧烈胎动。她想起昨夜在程远舟办公室发现的咖啡罐,
那些写着外文的药片并非胃药,而是抗排异反应的环孢素软胶囊。原来,
他一直在独自承受着病痛的折磨,却从未向她透露半句。凌晨三点的护士站空无一人,
寂静得让人害怕。林夏用程远舟的生日打开了他锁着的储物柜,铁盒里放着未拆封的奶嘴,
那是他对新生命的期待;还有沾着碘伏的穿刺针,见证了他与病魔无数次的斗争。
最底下压着苏蘅的死亡证明:2005年3月21日,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,享年十七岁。
这张薄薄的证明,承载着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,也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。
胎心监测仪的声响突然急促起来,如密集的骤雨。林夏蜷缩在丈夫病床旁,
指尖触到他后背的骨转移结节,那些凸起的颗粒硌着掌心,
让她想起新婚夜他背着她走过雪地时,军大衣纽扣的触感。那时的他们,对未来充满了憧憬,
却不知命运的阴霾早已悄然笼罩。“你知道苏蘅临终前说什么吗?
”程远舟的呼吸罩蒙着一层白雾,声音微弱而缥缈,“她说想看看海,
可那年渤海湾漂着蓝藻。”他艰难地从枕头下抽出牛皮纸袋,
新生儿脚印拓印旁附着脐带血配型报告。林夏的羊水在暴雨夜突然破裂,
豆大的雨点砸在窗户上,仿佛是命运无情的鼓点。程远舟正在进行第三次腰椎穿刺,
每一针都像是扎在林夏的心上。产房与肿瘤病房隔着长长的走廊,那是生与死的距离,
也是爱与痛的鸿沟。助产士惊呼胎心骤降的瞬间,
他监测仪上的血氧饱和度也同时跌破临界值,命运的天平岌岌可危。
当女儿的第一声啼哭打破黎明的寂静,那是生命的呐喊,也是希望的曙光。然而,
程远舟的瞳孔却开始逐渐涣散,生命的烛火在风雨中摇曳,即将熄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