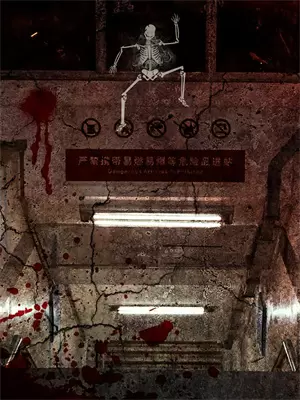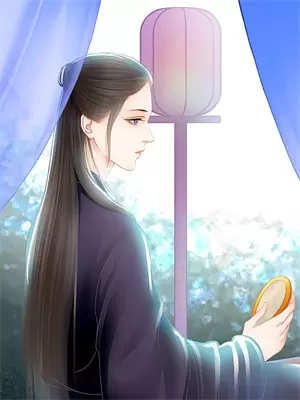一民国二十三年,秋分。我攥着那张泛黄的信纸,站在青石镇口时,雨丝正斜斜地织着网。
镇子卧在两山夹坳里,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亮,两侧黑瓦屋檐下挂着褪色的酒旗,
风一吹就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响,像谁在暗处翻着旧书。“后生,找哪家?
”卖麦芽糖的老汉掀开竹帘,浑浊的眼珠盯着我手里的牛皮箱。“寻槐记药铺,找沈先生。
”我把信纸往怀里塞了塞,指尖触到纸页上“救命”两个潦草的墨字,
那是表姑上个月托人从镇上捎来的,此后便没了音讯。老汉的脸瞬间沉了,
竹勺在糖锅里重重一磕:“槐记?你往西街走,尽头那棵老槐树下便是。不过劝你一句,
日头落了就别出门,尤其别沾老槐树的影子。”西街比镇口更显破败,墙根处长满青苔,
偶有门户开着,门后却总像有双眼睛在窥望。走到街尾,我果然看见一棵两人合抱的老槐树,
树身皲裂如老人的皮肤,枝桠歪扭地伸向天空,即便雨雾弥漫,也能看出枝上没有半片叶子。
树下立着间青砖木屋,门楣上挂着“槐记药铺”的匾额,漆皮剥落,
露出底下暗红的木头纹理,像干涸的血。“咚咚咚。”我叩响铜环,
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道缝,一股浓重的药味混着潮湿的土腥味扑面而来。“找谁?
”门后站着个穿月白长衫的青年,面容清瘦,眉眼间带着几分倦意,手里还拿着本线装书。
“我是林墨,从省城来,找表姑苏婉。”我递过信纸,“这是她托人寄给我的。
”青年接过信纸,指尖在“苏婉”二字上顿了顿,侧身让我进屋:“我是沈砚,
你表姑……半个月前失踪了。”药铺里陈设简单,柜台后立着排药柜,
抽屉上贴着泛黄的药名标签。墙角摆着张八仙桌,桌上放着盏油灯,灯芯跳动着,
将沈砚的影子投在墙上,忽明忽暗。“失踪?”我心里一紧,“怎么会失踪?
信里只说她在镇上遇到些怪事。”沈砚给我倒了杯热茶,
指尖泛着不正常的苍白:“青石镇怪事多,尤其这老槐树。你表姑上个月来镇上收药材,
住了没几天就说夜里听见槐树下有哭声,后来她偷偷挖开树根,说是发现了一口棺材。
”“棺材?”我端着茶杯的手一抖,热茶溅在手上,竟不觉得烫。“是口朱漆棺材,
棺身刻着缠枝莲纹,看着有些年头了。”沈砚的声音压得很低,“她那天慌慌张张跑来找我,
说棺材里好像有动静,可等我们再去看时,土坑是空的,棺材不见了。从那之后,
她就变得神神叨叨,总说有人跟着她,直到半个月前,她夜里出了门,再也没回来。
”我想起表姑信里的话:“槐下有棺,棺中有影,影随人走,索命断魂。
”当时只当是她胡言乱语,如今听沈砚一说,后背竟冒出一层冷汗。
“镇上其他人知道这事吗?”我问。沈砚摇头:“没人敢提。老槐树是镇上的禁忌,
据说光绪年间,镇上有个绣娘吊死在槐树上,从那以后,每年秋分前后,
都有人在树下看见穿红衣服的女人,还有人说,听见槐树下有刨土的声音。”正说着,
窗外忽然传来“沙沙”的声响,像是有人在挠窗户。我抬头一看,只见窗纸上贴着个黑影,
身形纤瘦,像是个女人,长发垂在肩上,随着风轻轻晃动。“谁?”沈砚猛地站起身,
抄起柜台后的药杵。黑影顿了顿,缓缓移开了。我跑到窗边推开窗户,外面雨还在下,
老槐树下空荡荡的,只有几片枯叶在地上打转。“是她吗?”我问。
沈砚脸色发白:“不知道,但这半个月,总有人在夜里来药铺窗外徘徊,每次都是这个黑影。
”那天夜里,我住在药铺后院的厢房。躺在床上,听着窗外的雨声和老槐树的“吱呀”声,
总觉得有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。迷迷糊糊间,我听见一阵细碎的脚步声,
从院外一直走到我的窗下,接着,有人轻轻叩了叩窗棂。“林公子,
救救我……”是个女人的声音,温柔又凄厉,像表姑的声音,又不像。我猛地坐起身,
摸出枕边的火柴点亮油灯,冲到窗边推开窗户。院中空无一人,只有老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,
像一只张开的大手,正缓缓向我伸来。二第二天一早,雨停了。
我和沈砚决定去老槐树下看看。树根处的泥土还很松软,能看出被人挖过的痕迹。
沈砚蹲下身,用树枝拨开泥土,忽然“咦”了一声,从土里挑出一枚银簪。那簪子样式老旧,
簪头是朵小巧的玉兰花,花瓣上还沾着些暗红色的污渍。“这是你表姑的吗?”沈砚问。
我接过银簪,指尖一颤。这簪子是表姑的陪嫁,她一直戴在头上,上次见她时,
还特意给我看过。“是她的。”我攥紧银簪,“她肯定来过这里,说不定还在附近。
”我们沿着老槐树的根须往外找,走到镇子东头的破庙时,沈砚忽然停住了脚步。
破庙的门虚掩着,里面传来一阵“叮叮当当”的声响,像是有人在翻东西。“谁在里面?
”沈砚喊了一声,推开门走了进去。破庙里蛛网密布,神像倒在地上,断了一只胳膊。
角落里,一个穿灰布衣衫的老头正蹲在地上,翻着一个破旧的木箱。听见动静,
老头猛地回过头,脸上沾满灰尘,眼神浑浊。“王老头,你在这干什么?”沈砚认出了他,
这是镇上的守墓人,平时住在山脚下的坟场里。王老头咧嘴一笑,
露出几颗发黄的牙:“找东西,找我丢的烟袋锅。”“你看见过一个穿蓝布衫的女人吗?
大概三十多岁,梳着发髻。”我问。王老头的目光在我脸上扫了扫,又看了看沈砚,
忽然压低声音:“你们是在找苏掌柜吧?我前几天在坟场看见她了,夜里三更,
她跪在一座新坟前,嘴里念叨着‘槐棺要开了’。”“新坟?谁的坟?”沈砚追问。
“不知道,坟前没立碑,就堆了些土,旁边还插着根红布条。”王老头站起身,
拍了拍身上的灰,“我劝你们别找了,青石镇的事,少管为妙,免得惹祸上身。
”从破庙出来,我们直接去了山脚下的坟场。坟场里杂草丛生,墓碑歪歪斜斜地立着,
风吹过,草叶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,像鬼哭。按照王老头的说法,
我们在坟场最里面找到了那座新坟,坟前果然插着根红布条,布条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
沈砚蹲下身,用手拨开坟上的草:“这坟堆得很草率,不像是正经下葬的。”我盯着红布条,
忽然觉得眼熟。这布条的颜色和纹理,竟和我昨天在窗纸上看见的黑影身上的红衣一模一样。
“挖开看看。”我咬了咬牙。沈砚愣了一下,随即点了点头。我们找了两根树枝,
开始刨坟上的土。土很松,没挖多久,就碰到了坚硬的木头。继续往下挖,
一口朱漆棺材渐渐露了出来,棺身刻着缠枝莲纹,和沈砚描述的一模一样。“是它。
”沈砚的声音有些发颤。棺材没有钉棺钉,棺盖是虚掩着的。我深吸一口气,
和沈砚一起推开了棺盖。棺里没有尸体,只有一件红绣袄,绣袄上绣着鸳鸯戏水,针脚细密,
像是新做的。绣袄旁边,放着一面铜镜,镜面蒙着层灰,我伸手擦了擦,
铜镜里忽然映出一个人影——穿红衣服的女人,长发垂肩,正站在我的身后。“啊!
”我惊叫一声,猛地转过身。身后空荡荡的,只有风吹着草叶晃动。沈砚也吓了一跳,
连忙问我怎么了。我指着铜镜,话都说不出来。沈砚拿起铜镜看了看,
皱眉道:“什么都没有啊。”我凑过去一看,铜镜里果然只有我和沈砚的影子,
刚才的红衣女人不见了。难道是我眼花了?“不对劲。”沈砚忽然说,“这棺材里的绣袄,
看着像是光绪年间的样式,和传说中吊死在槐树上的绣娘穿的衣服一样。”他话音刚落,
坟场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,紧接着,王老头领着几个村民冲了进来,手里拿着锄头和扁担,
个个怒气冲冲。“你们在干什么?!”为首的是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,是镇上的族长李老头。
“李族长,我们在找失踪的人。”沈砚解释道。“找什么人?惊扰了槐仙,你们担待得起吗?
”李老头气得吹胡子瞪眼,“老槐树是镇上的守护神,这棺材是槐仙的东西,你们竟敢挖开,
是想让全镇人遭殃吗?”“什么槐仙?这分明是口旧棺材。”我反驳道。
“你个外乡人懂什么!”王老头跳出来,“光绪年间,绣娘死后,镇上就出了瘟疫,
后来道长说,是绣娘的怨气不散,要把她的棺材埋在槐树下,让槐树镇着她,从那以后,
镇上才太平。你们挖开棺材,是想让瘟疫再回来吗?”村民们议论纷纷,个个眼神不善。
李老头挥了挥手:“把棺材重新埋好,再去槐树下烧点纸钱赔罪,至于你们两个,
赶紧离开青石镇,别再惹事。”没办法,我们只好跟着村民把棺材埋好。回去的路上,
沈砚悄悄对我说:“李老头在撒谎,我小时候听我师父说过,
当年的瘟疫是因为镇上的井水被污染了,和绣娘没关系。他这么紧张,肯定有问题。
”我点了点头,心里越发觉得奇怪。表姑的银簪出现在槐树下,
她又在新坟前念叨“槐棺要开了”,这一切似乎都和那口朱漆棺材有关。
而李老头和村民们的反应,更像是在掩盖什么秘密。当天晚上,
我和沈砚决定去李老头家探探情况。李老头住在镇子中心的大宅院里,院门紧闭,院墙很高,
墙上爬满了爬山虎。我们绕到后院,发现有棵老榆树,枝桠伸到了院墙上。“我爬进去看看,
你在外面接应。”沈砚说完,抱住树干,手脚麻利地爬了上去。我在墙外等着,
心里七上八下的。过了大概一盏茶的功夫,沈砚从墙上跳了下来,脸色比白天更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