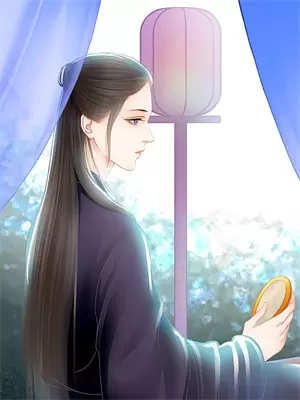村民离奇死在“赶尸”仪式的中央。尸体七窍流血,喉管被一种诡异的苗疆蛊术穿透。
老刑警认定是谋杀,证据却指向了“灵异”方向。当追查到德高望重的寨老时,
我看到了他平静下的癫狂。他借用“赶尸”的民俗掩盖死亡。所有的离奇死亡,
不过是他藏尸复仇的容器。寨老说:“今晚,你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
”01.踏进这片深山苗寨的时候,空气里弥漫的复杂气味就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
浓重的药草味,混杂着尸体腐败后特有的甜腻,
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类似香烛燃烧后的灰烬气息。我叫林默,
一个在市局重案组干了二十五年的老刑警。我这双手,
摸过的尸体比一些人一辈子见过的人都多。可眼前的场景,还是让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。
案发现场在寨子中央的一片空地上,一个所谓的“赶尸”仪式被打断了。地上躺着一具尸体,
穿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廉价西装,姿势僵硬得像是被人摆弄过的木偶。周围一圈,
插满了画着鬼画符的幡旗,地上散落着铜铃和黄纸,气氛诡异到了极点。
围观的村民一个个眼神惊恐,嘴里念念有词,没人敢靠近。他们看我的眼神,
不像是看一个来伸张正义的警察,更像是看一个不懂规矩、要触怒神灵的闯入者。“冲煞了!
是冲煞了!”一个老妇人哆哆嗦嗦地喊着,“赶尸的仪式走错了时辰,惹怒了山神!
”我心里升起一股无名火。“冲煞?”我冷哼一声,拨开拦路的村民,径直走向尸体。
干了这么多年刑警,我最烦的就是这种装神弄鬼的调调。在我的世界里,没有鬼神,
只有活生生的人,和他们犯下的罪。“林队!”身后传来一个清脆冷静的女声,是苏晴。
她是我们队里新来的法医,二十八岁,顶着犯罪现场学和毒理学的双硕士头衔,
是个理论知识储备量惊人的小姑娘。她提着勘察箱快步跟上来,戴上乳胶手套,
二话不说就蹲在了尸体旁边。“死者张大林,男,本地人,三十五岁。
”苏晴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,仿佛眼前不是一具恐怖的尸体,而是一份待处理的实验报告。
她仔细检查着尸体的口鼻、眼耳,然后眉头紧锁。“林队,你看这里。”我凑过去,
顺着她手指的方向,看到死者张大林的喉结下方,有一个极其细微的红点。
那个红点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,不仔细看,就像一颗普通的皮肤痣。
苏晴用镊子轻轻拨开那里的皮肤,一个针尖大小的孔洞赫然出现。“表面无外伤,没有扼痕,
没有挣扎迹象。”苏晴的声音变得凝重,“但这个孔洞,直接贯穿了喉管。
我怀疑是某种特殊的毒物,或者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器具所致。”我的心猛地一沉。
就在这时,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苏晴在提取死者血液样本时,发现血液的颜色不对劲,
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暗紫色。她当场做了快速毒物测试,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“林队,
血液里检测出了成分极其复杂的生物碱和毒素,
很多都匹配不上我们数据库里的任何已知毒物。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,作用机理不明。
”她顿了顿,抬起头,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困惑和一丝……恐惧。“我只能暂时称之为,
‘蛊穿喉’。”“蛊?”我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字。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,
这个词让我感到一阵生理性的厌恶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视线重新落回尸体上。我注意到,
张大林的双脚鞋底有非常特殊的摩擦痕迹,鞋尖磨损得厉害,而后跟却相对完好。
这根本不像是一个人自然倒地死亡该有的样子,倒更像是……被人抬着,
双脚在地上拖行了很长一段路。就像传说中,“赶尸匠”驱使尸体行走的样子。
现场的每一条线索,都在疯狂地把这起命案推向“灵异”的方向。就在这时,
围观的人群忽然安静下来,自动分开一条路。一个身形佝偻、满脸皱纹的老人,
拄着一根盘龙拐杖,缓缓走了过来。他穿着一身靛蓝色的苗族传统服饰,头发花白,
眼神却异常明亮。“是寨老!”人群中有人低声说。他就是吴山,
这个偏远苗寨德高望重的精神领袖。吴山走到我面前,浑浊的眼睛在我脸上打量了一圈,
然后看向地上的尸体,叹了口气。“林警官,这都是命数。”他的声音苍老而平和,
带着一种让人不得不信服的威严,“是我们寨子的宿命,您一个外乡人,还是不要深究的好。
惊扰了亡灵,对谁都没好处。”他的态度谦和有礼,可我却从他那双看似悲悯的眼睛深处,
捕捉到了一闪而过的、冰冷的审视,甚至……是一丝嘲讽。
我的怒火“噌”地一下就顶到了脑门。一个活生生的人,以如此残忍诡异的方式死去,
在这位德高望重的寨老口中,竟然成了一句轻飘飘的“宿命”。那些村民看我的眼神是恐惧,
而他看我的眼神,是蔑视。蔑视我的无知,蔑视我所代表的、在他看来软弱无力的法律。
“吴老先生。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说,“在我这里,没有宿命,只有谋杀。
只要是谋杀,我就一定会查到底。”我看到他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,
嘴角勾起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弧度。“那您,就请自便吧。”说完,他便转身,拄着拐杖,
慢悠悠地离开了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村民们对我投来的目光更加充满了敌意和戒备。
我心里清楚,从这一刻起,我要面对的,不仅仅是一个诡异的凶手,
还有这一整个被愚昧和迷信包裹的村庄。而那个看似与世无争的寨老,将是我最大的阻碍。
02.我的调查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。我试图走访村民,了解死者张大林的人际关系,
但所有人都对我避之不及。他们的嘴巴像是被什么东西封住了一样,无论我问什么,
得到的答案永远是摇头,或者是一句敬而远之的“我们不知道,你去问寨老吧”。寨老。
又是寨老。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寨子里,吴山的名字仿佛一道无形的圣旨,他的权威,
甚至超越了我身上的警服。我从侧面了解到,死者张大林在村里就是个恶霸,游手好闲,
欺男霸女,人缘差到了极点。但奇怪的是,就在最近,他好像变了个人,
不仅还清了所有欠款,还跟人说准备离开苗寨,到外面去打工。
一个准备金盆洗手、重新做人的人,为什么会突然死在“赶死”仪式上?
我让苏晴和技术队的同事对案发现场进行地毯式搜证,希望能提取到一些有用的痕迹物证。
可我们刚一动土,就被一大群村民围住了。“不能挖!不能动土!”“会惊动山神的魂!
你们会给寨子带来灾祸的!”村民们群情激奋,一个个用身体挡在前面,
大有我们再敢动一下就要拼命的架势。而煽动这一切的,
正是那个“恰好”路过、前来“劝解”的寨老吴山。他站在人群后面,
一脸“为难”地对我说:“林警官,民意难违啊。这也是为了你们好。
”我气得几乎要当场发作。舆论压力瞬间全部倒向了我这边,
我成了那个不尊重民俗、要给寨子带来厄运的罪魁祸首。调查被迫中止。
回到临时搭建的指挥部,我一拳砸在桌子上。“欺人太甚!”“林队,别生气。
”苏晴递过来一杯水,她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冷静,“发火解决不了问题。他们越是阻挠,
就越说明这里面有鬼。”她指了指桌上的一排证物袋。
“我把现场残留的那些草药带回来化验了。你猜我发现了什么?”我看向她。
“其中几种药草的混合物,燃烧后会产生一种具有强烈致幻和神经麻痹效果的气体。
虽然剂量很小,但如果在一个相对密闭或者空气流通不畅的环境里,足以影响人的神志。
”我的眼睛亮了起来。这至少证明了,所谓的“灵异”,是有科学依据的。
“还记得尸体脚上的摩擦痕迹吗?”我问。苏晴点点头:“记得。
我推测尸体是被拖行或者‘抬着’移动的。”“没错。”我站起身,走到地图前,
指着案发现场的位置,“如果凶手要运送一具尸体到这里,他不可能走大路。
他一定会选择一条更隐蔽的路线。”我的手指,
最终点在了地图上一条蜿蜒曲折、几乎被废弃的山路上。根据我打听到的消息,那条路,
就是寨子里流传已久的,古老的“赶尸”路线。我决定亲自去走一趟。苏晴不放心,
坚持要跟我一起去。我们沿着那条被杂草覆盖的小路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里走。
路两旁的树木越来越茂密,光线也变得昏暗起来。空气里飘荡着一股潮湿的腐叶气息,
安静得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和喘息声。走着走着,我忽然感觉头脑一阵发晕,
眼前的景象开始变得模糊、扭曲。苏多晴的情况比我更糟,她脸色苍白,
扶着一棵树干呕起来。“林队……这空气……有问……”她话还没说完,就软软地倒了下去。
我急忙扶住她,可我自己也感觉天旋地转,视线里出现了重影。我看到前面的山路上,
影影绰绰地出现了几个人影。他们穿着古旧的衣服,身体僵直,一蹦一跳地往前走。
在他们身后,一个穿着道袍的男人,手里摇着铜铃,口中念念有词。是“赶尸”的队伍!
我的大脑告诉我,这是幻觉,是那些致幻草药在作祟。可那画面太过真实,
铜铃声仿佛就在耳边响起,一声声敲击着我的神经。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,脚步虚浮,
一步步地朝着悬崖边走去。山涧的风吹来,带着一股刺骨的寒意,我猛地打了个激灵,
瞬间清醒了一半。我低头一看,自己的半只脚已经悬在了悬崖外面!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
一根粗糙的拐杖伸了过来,用力地将我往后一拉。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,
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冷汗湿透了我的后背。寨老吴山那张布满皱纹的脸,
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他“恰巧”出现在这里,一脸关切地看着我。“林警官,
都说了让你们不要乱闯。这山里的瘴气,厉害得很。你们不敬神灵,冲撞了山神,
是会受罚的。”他一边说,一边从怀里掏出两个小布包,递给我和苏晴。
“这是我们寨子里的解瘴丹,闻一闻就好了。”我接过布包,一股清凉的草药味钻入鼻腔,
眩晕感立刻减轻了不少。我看着他,心里一片冰冷。瘴气?不。这不是什么该死的瘴气,
这是一个陷阱!一个由他亲手布置的、利用毒草和地形制造的陷阱!
他算准了我会来走这条路,他算准了我们会中毒,他甚至算准了自己“恰好”出现的时间。
他不是来救我们的。他是来警告我,用这种方式,进一步加深这起案件的“灵异”色彩,
让我知难而退。我从地上站起来,拍了拍身上的土,眼神死死地盯着他。从一开始的焦躁,
到此刻的警惕。我的直觉,前所未有地清晰——眼前这个看似德高望重、慈眉善目的老人,
就是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。第一次正面交锋,我输了。但我心里的斗志,却被彻底点燃了。
03.三天后,就在我们对张大林的死一筹莫展的时候,第二具尸体出现了。死者叫李强,
一个来寨子附近谈生意的外地商人。他的尸体是在另一条山路上被发现的,
那条路同样是传说中“赶尸”的必经之路。而他的死状,与张大林,一模一样。
七窍流着暗紫色的血,喉咙上,同样有一个针尖大小的、被苏晴称为“蛊穿喉”的致命伤口。
“林队,两具尸体喉管上的伤口,我用高倍显微镜比对过了。”苏晴的办公室里,
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,“直径、深度、角度,分毫不差。这绝不是意外,
而是出自同一个凶手,同一种工具,同一种极度专业化的手法。”我盯着两份尸检报告,
脑子里飞速地运转着。两个死者,一个本地恶霸,一个外地商人。
同样的死亡地点——“赶尸”路。同样的死亡方式——“蛊穿喉”。这其中,一定有关联。
“查!”我命令道,“把李强和张大林的所有社会关系都给我翻个底朝天!
我不信他们之间毫无交集!”两天后,结果出来了。结果让我浑身一震。李强和张大林,
十年前,不仅是老同学,还共同参与了一起轰动一时的“权贵子弟肇事逃逸案”。
案卷上记录着,十年前,一个由权贵子弟组成的飙车团伙,
在深夜撞倒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苗族女孩,导致其重伤。而李强和张大林,
就是当时车上的两个帮凶。他们不仅没有施救,反而帮助主犯逃逸,并动用家里的关系,
在后续的调查中毁灭证据,颠倒黑白。最终,那起案件因为“证据不足”,主犯逍遥法外,
只赔了一笔钱了事。而被撞的那个无辜的苗族女孩,在医院躺了半年后,因为重伤不治,
最终死亡。我的手指,抚过案卷上那个女孩的名字。吴晓月。而她的爷爷,正是寨老,吴山。
所有的线索,在这一刻,都串联了起来。复仇。这是一场蓄谋已久、跨越了十年的复仇。
我立刻推翻了之前的所有假设。凶手根本不是想在“赶尸”仪式上杀人,
他只是在利用“赶尸”这个古老的习俗,作为他运送和抛弃尸体的工具!
他先在别处将目标人物残杀,然后利用“赶尸”这个充满灵异色彩的民俗,
将尸体运送到预定地点,再伪装成“仪式失败”或者“意外暴毙”的假象。这样一来,
既能处理尸体,又能将警方的视线引向“鬼神之说”,为自己创造完美的脱罪屏障。
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。好一个,高智商犯罪。我的胸口剧烈起伏着,
一股夹杂着愤怒和震惊的情绪直冲头顶。我拿着案卷,直接冲到了吴山的住处。
他正坐在院子里,悠闲地编着竹筐,仿佛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。“吴老先生!
”我把卷宗用力地拍在他面前的石桌上,“张大林,李强,这两个名字,您不陌生吧?
”吴山抬起眼皮,慢悠悠地看了我一眼,又低头继续忙活手里的东西。“不认识。
”“不认识?”我冷笑一声,“那吴晓月呢?您孙女的名字,您总该记得吧!十年前,
就是他们,害死了你的孙女!”吴山编竹筐的手,停顿了一下。仅仅是那么一瞬间。然后,
他抬起头,脸上露出了悲伤又无奈的表情。“林警官,往事就不要再提了。晓月她……命苦。
至于你说的什么张大林李强,我确实不认识。”他演得太好了。那份悲伤,那份隐忍,
足以让任何一个不了解内情的人为之动容。“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,
”我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,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丝破绽,“有人看到您也在附近出现过。
您当时在做什么?”“哦,”吴山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,“我是去为他们运送尸体的。
我们苗家的规矩,客死异乡的人,都要由寨老请法师‘赶’回故乡安葬。
我只是在维护我们的传统。”他顿了顿,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讥诮。“林警官,
您不会连我们寨老尽一份心意,都要污蔑成杀人凶手吧?”我被他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是啊,他是寨老,他是精神领袖。他出现在任何“非正常死亡”的现场,
都可以用“维护传统”“安抚亡灵”来解释。这个身份,是他最完美的保护色。
看着他那张德高望重、悲天悯人的脸,再联想到他孙女惨死的真相,
一股巨大的荒谬感和愤怒感席卷了我。他利用了所有人的同情,利用了古老的民俗,
将一场残忍的连环谋杀,包装成了一出迟来的、悲壮的“天道轮回”。而法律,
在这个被他一手打造的舞台上,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我的愤怒达到了顶点,但我的思路,
也前所未有的清晰。我必须,揭开他这张伪善的面具。04.回到指挥部,我陷入了沉思。
吴山的心理防线太强大了,他用整个寨子的民俗和自己的悲惨遭遇,
给自己构建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。没有直接证据,我根本动不了他。“林队,
法医报告有新发现了!”苏晴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思绪,她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报告,
脸上带着一丝兴奋和凝重。“我们在第二具尸体,也就是李强的脚踝皮肤深层,
提取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药膏残留物。”“药膏?”“对。
”苏晴指着报告上的化学成分分析,“这种药膏的主要成分是一些罕见的草药,
具有极强的防腐和肌肉僵化作用。简单来说,它能暂时性地保持尸体的外观稳定,
让尸体看起来像是刚死不久,并且……非常僵硬。”非常僵硬。这四个字,像一道闪电,
劈开了我脑中的迷雾。我想起了“赶尸”的传说,那些被符咒控制、一蹦一跳行走的尸体。
“苏晴,”我的声音有些发干,“你大胆推测一下,
有没有一种可能……死者在所谓的‘赶尸’仪式开始前,就已经……濒死了?
”苏晴的眼睛猛地睁大,她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。“我明白了!”她激动地一拍桌子,
“凶手先给目标人物下一种慢性毒药,或者用某种手段使其进入假死或濒死状态。然后,
他给‘尸体’涂上这种能维持僵硬的药膏,将其伪装成‘赶尸’的对象。”“接着,
”我接过了她的话,“在‘赶尸’的仪式进行到途中时,凶手再通过某种方式,
引爆目标体内的致命毒素,造成其‘当场死亡’的假象!而那个所谓的‘蛊穿喉’,
很可能就是毒素爆发后,从内部破坏喉管组织形成的最终效果!”我们两个人对视一眼,
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震惊和骇然。我终于明白了。我终于明白了那个最核心的诡计!
寨老吴山,这个精通苗疆蛊术和草药知识的魔鬼,他根本不是在“藏尸”。他是在“造尸”!
他把那些活生生的仇人,一个个变成了他复仇仪式上的道具!
他让仇人在所有村民的“见证”下,在最符合民俗、最充满“灵异”色彩的场景中死去。
那些死者,从一开始,就是他复仇计划里,一个个被精心摆放的“容器”!
这个真相的残酷和精妙,让我不寒而栗。“马上!立刻!调取过去十年,
所有在这个苗寨及周边地区,在‘赶尸’途中发生意外死亡的卷宗!
”我冲着身边的警员大吼。我的大脑在飞速运转,冷汗顺着额角滑落。吴山的复仇,
绝对不止这两个人。半小时后,一份名单摆在了我的面前。五起意外死亡事件。五个死者,
身份各异,有游客,有商人,有地质勘探队员。
但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——经过我们紧急排查,这五个人,都或多或少地,
与十年前那起“权贵子弟肇事案”的利益链条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有的是当年帮忙做伪证的,有的是帮忙打通关节的,
有的是收了黑钱压下舆论的……吴山的复仇名单,远比我想象的要长。“立刻申请逮捕令!
马上对吴山实施抓捕!”我拿起对讲机,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。这个隐藏在迷雾中的恶魔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