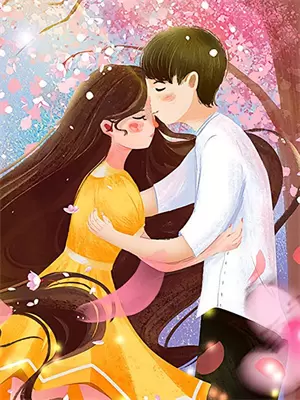1 尘封的抽屉屋檐下的雨一滴一滴地落在青石板上,像是有人在细数时间。
林素把手里的箱子轻轻放在地上,灰尘在光影中浮动,她有些恍惚。那是母亲的老屋,
砖木结构,年久失修。墙上的日历停在“1986年”,窗台上仍搁着一只泛白的搪瓷缸,
里面的竹子早已枯成空壳。母亲去世后,她一直没敢回来。直到今天,
她才鼓起勇气回来整理这座房子。老屋里弥漫着淡淡的樟脑气味,那是母亲最喜欢的气味。
林素打开柜子,一叠叠泛黄的床单、旧毛衣、缝补过无数次的棉被静静躺着。她翻着,
像是在掀开一个个旧日的梦。当她打开最底层的抽屉时,一封旧信滑了出来。
那是一封浅蓝色信纸,上面印着几片淡粉色的樱花。信封的角有点卷曲,信口没有封,
纸的边缘被岁月磨得发脆。她愣了几秒,才伸手拿起来。信封上,
是她自己年轻时的笔迹——圆润、带着少女特有的矜持:致:李牧生林素的呼吸顿时乱了。
那个名字,她已经有四十年没有念出口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984年的夏天,
风吹过凤凰镇的稻田,林素刚从师范学校毕业,穿着白衬衫、蓝裙子,站在镇口的邮局门口。
那时她的心里藏着一个名字,一个不敢轻易提起的人。李牧生。他是镇中学的代课老师,
教物理。那年她实习,他帮她修过一次坏掉的录音机,从此她的心也跟着录音机的磁带,
一圈一圈地绕进了他的声音里。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卡其布衬衫,
笑起来眼角有细微的皱纹。那年他二十五岁,她二十。可惜,那个年代,喜欢不能说出口。
她写了好几封信,练习了无数遍称呼,始终没有寄出。那天,她把信放进抽屉,
说:“等我再勇敢一点。”可后来,父亲病重、母亲催她回城,她被分配到县一小教书,
李牧生也调去了隔壁县。那封信,就留在了抽屉的角落里,一留就是四十年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林素坐在木地板上,
手指抚过信封。里面的纸张轻轻晃动,像有风吹过她的青春。她犹豫了很久,终于抽出信纸。
“牧生: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出去,也许永远都寄不出去。可有些话,不写下来,
我怕这一生都憋在心里。你说过,世上的事情不必太急,风迟早会吹过屋檐。可我等了很久,
也没等到那阵风。今天傍晚我看见你在操场上和学生们笑,那一刻我忽然想,
如果我能留在镇上教书就好了。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有一点喜欢我,但我希望有。
哪怕只有一点,也足够我记一辈子。素”字迹细长,尾笔轻颤。
她看得出那是二十岁的自己在忍着激动写下的。那时候她还相信,只要勇敢一次,
就能改变命运。林素读着,嘴角微微发苦。那封信,她记得写了整整一个晚上。
后来母亲来敲门,她赶紧藏进抽屉。第二天就回了县里,从此再没回来。她靠在墙边,
轻轻叹了口气。窗外的雨渐小,天空透出一线微光。第二天,林素叫来废品收购的老李,
把一些坏掉的木柜搬出去。老李是她旧邻居,看她翻箱倒柜,笑着说:“林老师,
您这老屋里还真是个宝藏,啥都有。”林素也笑:“是啊,连我自己都快认不出来这里了。
”“要不是前两年镇上扩路,我还以为您早搬走国外去了。”“哪儿也没去。”她淡淡地答。
老李想了想,又说:“李老师前阵子还提起过您呢。”林素的手一顿:“李老师?
”“就是原来那位教物理的李牧生啊,现在都七十出头了,听说搬去市里跟儿子住了。
”那一刻,林素的心忽然跳得很快。四十年,那个名字竟然还存在于某个角落里。
她没问更多,只是点点头:“哦,他……还好吧?”“挺好的,前几年还来镇上看老朋友。
”林素笑了笑:“那就好。”可那天晚上,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那封信就放在枕边,
她一闭眼就能看见李牧生的样子——夏天的阳光下,他推着自行车,笑着对她说:“小林,
别怕,试着去讲一节课,你会讲得很好的。”那一刻,她觉得整个青春都被照亮了。
——第二天清晨,她把信重新叠好,放进信封。手指在信口停留了很久。她忽然觉得,
这封信不该再被藏在抽屉里。哪怕李牧生从未收到,也该让它去流浪一次。
她找出一个新的信封,把旧信包在里面,又在信纸上写了几行小字:若你看到这封信,
请不要惊讶。只是我终于鼓起勇气,替年轻的自己,寄出她当年的心意。她拿起信,出了门。
外面的阳光正好,雨后的空气带着青草味。邮筒仍在街角,只是颜色褪成浅绿,
铁皮上有些斑驳。她走过去,手悬在空中。风从她的掌心穿过。片刻后,
她微笑着把信塞进邮筒。那一刻,阳光照在她的发上,银丝闪了一下,
她忽然听见了远处孩子的笑声,像极了1984年的夏天。2 寻人启事几天后,
邮递员的到访打破了林素的平静。那是一个阳光正好的上午。
老屋外的樱桃树结了第一茬果子,鸟儿在枝头啄食。林素正蹲在门口擦一只旧铜壶,
忽然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。“林老师,有您的信!”邮递员是个年轻小伙子,
穿着蓝色的制服,笑得腼腆。他递过来一个浅黄色的信封,上面印着邮政退件章。
林素愣了几秒,才接过。信封熟悉得让她心口一紧——那正是她前几天寄出的那封信。
退回的理由印得清清楚楚:收件人不详,地址不存在。她的手指轻轻颤抖,
信封的边缘在阳光下泛白。她没想到,时隔四十年,她终于鼓起勇气寄出的信,
竟然又回到了她的手中。那一刻,她心底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荒凉。原来,
时间真能抹去一个人的踪迹。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屋里,尘埃在光柱中漂浮。
林素坐在老藤椅上,一遍又一遍看着那行退信的字。
她突然有种奇怪的冲动——想知道李牧生现在在哪里。他真的搬去市里了吗?他还健在吗?
他是否也曾想起过那个夏天、那个在讲台上紧张发抖的女实习生?那种被时间隔开的思念,
像是一条不肯干涸的小河,静静流淌。她想起了老李的话:“他前几年还来镇上看老朋友。
”也许还能找到线索。第二天一早,她穿上浅灰色的风衣,搭上去县城的早班车。
县城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。小广场成了商场,旧电影院改成了连锁药店,
邮局那面红砖墙还在,只是门口的邮箱早已换成亮绿色的新款。林素走进去,
柜台后坐着一位中年女职员。她说明了来意,小心翼翼地拿出那封退回的信。“您好,
我想问问,这个收件地址是不是已经改成别的地方了?以前在凤凰镇中学旁边的教师宿舍。
”女职员接过信,看了看:“哦,这个宿舍区早在九几年就拆迁了。
那批教师都分配去新城区了。”“那请问,您知道原来住在那儿的李牧生老师,
他后来搬哪去了?”“李牧生?”女职员抬头想了想,“我记得这个名字,
好像前几年我们单位办过老教师慰问,有个李老师是他亲戚。当时留过个电话。
”她翻了翻抽屉,从一本厚厚的通讯簿里撕下一页小纸条。“您试试看这个号码吧。
”林素双手接过,连声道谢。回到老屋时,天色已晚。风从屋檐下穿过,吹动窗帘。
她坐在床边,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。拨通电话的那一刻,她的心跳几乎能听见。“喂?
您好,请问您是李老师的亲戚吗?”电话那头是个男声,
带着几分迟疑:“您说的是……李牧生老师?”“是的,我是他的旧同事。”她犹豫了一下,
补充道,“也算老朋友。”那边沉默了几秒。“您可能不知道,李老师……三年前去世了。
”林素怔住,手机差点滑落。“他走得很安详,是心脏病。后来我们帮他整理遗物时,
还看到过一封写着‘林素’名字的信,不过已经泛黄看不清了。我们猜是他以前的同事,
就没敢动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温和而平静,可每个字都像石子落在林素心湖里,一层层晕开。
她哽咽着问:“那封信……您还记得在哪里吗?”“放在他书桌的抽屉里,
后来搬家丢了不少东西,不知道还在不在。要不,我把他的旧屋地址发您,您可以去看看。
”“谢谢。”她低声说。挂掉电话,屋里只剩下风声。那一夜,林素几乎没合眼。
她望着天花板,脑海里不断浮现那个名字。原来,他也给她写过信。可惜,
两封信隔着四十年的时光,终究没能相遇。第二天清晨,她背上一个帆布包,
坐上了去市里的长途车。窗外的公路在阳光下闪烁,油菜花一片金黄。她靠在窗边,
心里却空空的。城市比她想象的更大。根据对方给的地址,她在一栋老旧居民楼前停下。
铁门生锈,信箱歪歪斜斜。三楼的一扇窗半开着,窗台上放着一盆凋谢的君子兰。
邻居告诉她:“李老师以前就住这儿,去世后儿子把屋子留着没动。”她敲了敲门。
无人应答。门口贴着一张泛黄的便签,上面写着:“如有旧信件,请放入信箱。
”林素轻轻笑了。命运似乎喜欢用这样的方式,与她捉迷藏。她打开帆布包,
把那封被退回的旧信放进信箱。然后又拿出一张新的信纸。
她写下几行字:牧生:四十年过去,我终于有勇气再来找你。听说你也曾为我写过信。
如果我们能早一点互相找到,也许故事会不一样。可我不再遗憾了。因为现在,我至少知道,
你也曾记得我。素她把信叠好,放进信箱,与那封退信静静叠在一起。风从长廊吹过,
带起一阵淡淡的花香。那一刻,她忽然觉得,这一趟,不是去找他,
而是去完成自己未竟的青春。她转身下楼。夕阳从楼缝里透出一线金光,照在她的肩上。
她想,或许这就是告别最温柔的样子。当晚,她住进市区一家小旅馆。夜深时,她站在窗前,
看着街灯一点点亮起。她忽然想,也许明天可以去他生前的学校看看。毕竟,
那才是他们故事开始的地方。窗外的风吹动窗帘,她轻声呢喃:“牧生,
我还记得你修好的那台录音机——它还能放。”她笑了,笑里带着泪。
3 重返校园翌日的阳光格外明亮。林素早早醒来,收拾好行李,把头发简单挽起。
镜中的她眼角已有细纹,但那双眼睛依旧澄澈——那是岁月无法磨去的清光。
她站在公交站牌下,车驶来的风掀动她的衣角。车上坐着放学路上的学生,
叽叽喳喳地谈笑着,背包上挂着卡通钥匙扣。那一幕让她忽然有些恍惚——当年,
她也曾那样年轻,提着笔记本、怀揣理想,从师范学校分配到凤凰镇中学实习。而那里,
正是她与李牧生初遇的地方。公交车缓缓驶过城区,拐向郊区的旧路。
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得熟悉:那条河依旧在,
河岸的柳树比记忆里更粗壮;老桥换了水泥栏杆,却依稀能辨出当年他们并肩走过的轮廓。
她下车的时候,正好是午后两点。凤凰镇中学的新校门很气派,门楣上嵌着金色的校名。
可当她走进教学区的深处,老教学楼还在。红砖斑驳,窗框的漆早已剥落,
门口那块“实验中学”木牌上甚至还有李牧生的笔迹——那是他当年亲手刻的。
她轻轻抚摸那道痕迹,指尖微微颤抖。“您找谁?”一个年轻的男老师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。
“您好,我是来看望老同事的。”她顿了顿,又加上一句,“四十年前,我在这里实习。
”年轻老师一愣,随即笑了:“那您应该认识李牧生老师吧?
我们办公室还留着他的旧讲义呢!”林素怔住,喉咙有些发紧。“他在这里教了很多年吧?
”“对啊,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前辈。语文组每次新老师入职,都会有人提起他,
说他讲课特别有感染力,还爱给学生读诗。”“他确实喜欢诗。”林素轻声说,
“我记得他最喜欢《再别康桥》。”“是的!”年轻老师眼睛一亮,
“那首诗还印在我们校刊的封底呢!”他带她进了办公室,
从一个旧柜子里翻出一本厚厚的讲义。封面发黄,边角卷起。
第一页是李牧生的字迹——“语文,不只是文字的技艺,更是心灵的温度。
”林素抚着那一行字,眼眶微热。那是她记忆中的字,也是他写信时的笔触。
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,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她手背上。年轻老师忙着倒水,
她轻声问:“他后来……还结婚了吗?”老师犹豫了一下,点头:“结过。
夫人是我们学校的图书管理员,可惜早走了。听老教师说,他后来一直独居在学校边的宿舍,
喜欢种花,最爱栀子。”“栀子……”林素喃喃重复,心底掠过一阵酸楚。
当年他们一起种过一株栀子花,她离开后,花就再没开过。
她忽然想起什么:“他留下的教案还在吗?我能看看吗?”年轻老师翻出一叠旧纸。
纸张发脆,墨迹微褪。其中一页,是李牧生写给学生的评语:“人生的意义,
不在于我们走得多远,而在于是否带着温柔与真诚去看每一个人。”那句评语下方,
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:“——素,你也要一直温柔下去。”林素的呼吸一下滞住。
那一行字显然不是写给学生的。她盯着那页纸,良久没有出声。泪水终于从眼角滑落,
滴在纸上,晕开浅浅的水迹。傍晚时分,学校的钟声响起。学生陆续从操场离开,
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林素站在走廊尽头,看着天边的橘红色光晕。风从窗口灌进来,
带着粉笔灰的味道。她忽然觉得,这里从未真正改变过。年轻老师走过来:“林老师,
您要不要去看看李老师以前的宿舍?就在操场后面的小楼。”她点点头。
宿舍楼的门锁早已生锈。年轻老师用钥匙打开门。屋子里满是灰尘,
但摆设还在:一张旧书桌、一盏台灯、几本书整齐地叠放。书桌上摆着一个木盒,盖子微掀。
林素小心地打开它——里面是一叠旧照片、几张学生贺卡,还有一张泛黄的信纸。
她轻轻展开那张信。信开头的名字是她。“素:见字如面。你走后,
我每次上课都不自觉地望向那扇窗。那棵栀子树长高了,风吹过时,像极了你笑的样子。
我不知道该不该写信给你。你有更远的路,而我,只能留在原地。但若有一天,
你再路过凤凰镇,看到那棵树,请替我浇一次水。我想,它会再次开花的。
——牧生”林素的手微微颤抖。那封信,从未寄出。就像她那封一样。
命运仿佛爱开玩笑——两封信,隔着四十年,终于在同一双手里重逢。她慢慢合上信纸,
放回木盒。眼泪滴在盖上,砸出一点透明的印痕。年轻老师轻声问:“这是您朋友写的吗?
”“是的。”她抬起头,笑得很温柔。“现在看来,他比我勇敢多了。”离开学校时,
天已黑。操场的灯亮着,学生在练歌,合唱的声音在夜风中飘荡。林素站在校门口,
最后望了一眼。那片灯火仿佛穿越了时光,映照着她年轻的影子。她想,
也许信不一定要送达。有些情感,只要被真心写下,就已经抵达了彼此的心。
她轻轻呢喃:“牧生,我替你浇了水。”夜风吹过,远处的栀子花香,淡淡袭来。
4 往事的门,轻轻开了一道缝那一夜,风从北边吹来,夹着淡淡的桂花香。林音坐在窗前,
手边的热茶已经凉透。她盯着那封泛黄的信,一遍又一遍地读。字迹早已微微晕开,
像是一个人记忆中反复回想的面孔——模糊,却温柔。信的开头是:“阿沈——”这两个字,
让她的心轻轻一颤。她几乎能听见当年的自己在提笔时,心跳声有多快。
那时的林音刚大学毕业,留着学生气的短发,写信的时候特意选了那种浅蓝色的信纸,
上面印着小小的鸢尾花。她写完信后,却迟迟没有寄出。——“我怕我们见面之后,
连朋友都做不成。”那是她在信里写下的最后一句。林音记得,当年沈之尧送她去车站。
她背着行李箱,他提着她那只掉漆的铁皮箱子。站台的汽笛响起时,她看见他嘴唇动了动,
却什么也没说。火车缓缓开动,她回头时,只看到他立在原地,像被风吹散的旧梦。那一别,
竟成了半生。如今,她坐在老屋的灯下,手指抚过那句“连朋友都做不成”,竟有些想笑。
那时的自己,是多么倔强,又多么害怕。她怕被拒绝,怕打扰他的人生,也怕那封信寄出后,
一切就此尘埃落定。于是她选择了“留白”——可她没想到,留白也会成为一种终身的遗憾。
第二天,林音把信装进一个干净的信封里,信封外没有地址。她只是想带着它出门走走。
十月的阳光落在她肩上,她走过老街的石板路。街口那家修表铺还在,门口摆着几张椅子,
坐着几个老人晒太阳。她停下脚步,看着那扇旧门。记忆中,
她和沈之尧就是在那家铺子门口告别的。那时他说:“等你回来,我们再去看场电影。
”她笑着答:“好啊。”只是,那场电影,终究没能看成。老屋的街区已经拆了一半,
修表铺也换了人。一个中年男人从里面探出头来:“阿姨,修表吗?”林音愣了一下,
笑笑:“不修,我就是路过。”她走到邮局门口,邮局的牌子是新的,
但门口那棵老槐树还在。阳光从枝叶缝隙洒下来,像碎碎的金粉。她看着信,
又抬头望向邮筒。忽然,一种冲动在心里升起——也许,她可以去找找他。就算什么都不说,
也只是想看看,他是不是还好。那天晚上,她在床头翻出一本旧日记。